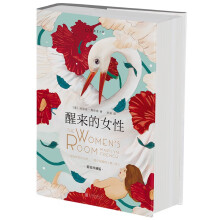太阳沉落之后,原野在那片黛紫色的云霭下耐心等待了许久。漫冈的草尖尖上,闪烁着阳光未曾燃烧净尽的火星子。那一整个夏天,夜都是来得这么磨磨蹭蹭。直到它终于将那些金灰色的萤火虫,一只只收进自己的黑口袋,疲倦地匍匐歇息,浑蓝的天空才突然一下子不见了。钻过围墙东头那个破土洞时,她的舌头死死抵住了自己的牙缝,唯恐那怦怦乱跳的心,真会弄出什么动静。鼓鼓的帆布书包,蹭着洞壁啪啪直往下掉沙粒,在静悄悄的野地里,像军训实弹演习时落地的炸弹崩响。那会儿她浑身的毛发都一根根竖了起来,头上一对刷子似的小辫儿变得硬邦邦,好险没把她自个儿卡住在洞口。一阵苦涩的蒿草气息扑面而来,这是围墙外才有的青草味。她直起身子,望见那片空荡迷茫的旷野,模模糊糊,像一团弥散的浓烟。她深吸一口气,又袅袅地吐出去,站定了,惶惶四顾。他在哪里?凉丝丝的夜露,伏在密匝匝的草叶上,蛇一般地从脚脖上爬过,又缠在鞋面上,脚指头粘湿滞重起来。在江南冬天的水田里踏荸荠,瑟瑟搜寻稀泥中坚冷的硬块。初中最后一年下乡劳动,依依哭着离开那田埂上铺满蚕豆苗苗的小村落。这农田鞋下,是土豆地,头上是高梁穗、苞米须子,如重重叠叠的围墙,重重叠叠的黑夜。穿过去、穿过去,却总也穿不过去……他呢?手电筒早已攥出了汗,一截刚刚洗净的紫皮甘蔗。假如按亮它呢,就只按一下。夜如此严厉陌生,吞没了树影和最后一线晚霞,连灰蓝的天空,连银白的星星,连油绿的风,连迅疾包围她的那些蚊子,都掩藏得不见踪影,只留下一片嗡嗡的声浪。嗬,北大荒,望不见一星灯光、一点渔火的寂寂原野,才有这样无边无际的夜,这样无穷无尽的黑色。像开春时浸透雪水的油黑的土地,黑得那么全心全意……手里的电筒终于闪了一闪,从她头顶的一棵小榆树梢忽地掠过。她打了一个寒噤。几道横七竖八的铁丝网,从围墙顶端匍匐过去,在黑暗中发着幽幽的冷光,如一面巨大的网,从天空俯撒下来。土墙的拐角上,两座残破的岗楼依稀可辨,遥遥相对,像两只窥探的眼睛,鬼鬼祟祟地眨动……到了放风时间?脚下会有纸团扔过来?也许就要高呼口号,将热血染红铁窗。英雄为什么总是要被囚禁?无论怎样牺牲都是英雄……那曾是多么虔诚的渴望。可恨晚生了十年,铁丝网的象征竟会有如此根本的区别——大批大批的知青代替了那些蓬头垢面的劳改犯。这残留的土墙、岗楼、嘹望台……时时提醒着他们,这是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劳改农场、劳改……她毛骨悚然。她从未一个人在墙下独处。尤其在野外,在簌簌夜风中,那个巨大的黑影,像一座墓冢、一个牢笼、一个洞穴,渗出阴森森的凉气。蒿草塞率响动,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关掉手电!”一双温热的大手,从身后环过来。她闻到一股熟悉的气息,热烘烘的汗气与烟味混杂的男人的气息。她把头靠在那宽宽的肩上,舒了口气;又紧紧箍住了他的脖子,把身子缩成一团,埋进他怀里。他很快放开她,侧过身子,如一只竖起耳朵的警觉的猎犬,急急地说:“听!什么声音?”……像是冬天旷野里秃秃的电线杆上怒吼的北风;像是融雪天野甸里远远的狼嚎;像是开闸奔涌的河水,哀怨悲怆地旋转;又如一群受了伤的小鸟,在嘤嘤地诉说什么……一种忽高忽低、忽强忽弱的颤音,参差不齐地从围墙里隐隐传来。“是哭声。”她说,“我们排的南方女生,刚才全哭了。”“哭什么?”“她们收到家里来信,钱塘江发大水了,要冲进城里来……有人说,见不到姆妈了。一个人哭开了头,两个人哭,最后大家都抱在一起哭了起来,阿丽哭得抽筋……”他打断她:“把手绢给我。”“做啥?”“给我。”她摸出手绢递他。手绢叠得方方正正,有一股香皂味儿。他在手里捏了一把,还给她。好像,笑了一笑。“想不到,你倒没有哭嘛。”“是没有哭。”她也笑笑,“她们刚刚开始哭,我就走出来了。”小时候,妈妈去上班,她可以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哭到妈妈回来。妈妈!可她自打离开家,就没给妈妈写过信。她哭什么?眼睛鼻子,都麻麻木木。“有没有人看见你出来?”他想想,追问一句。“没有。她们只顾哭了。”“郭春莓呢?”“她也没有哭。去寻杨大夫了,说要给大家打镇静剂。”“哦。毛巾牙刷带没带?”“带了。还有钱和粮票……”他默不作声,她听见他把手指关节捏得咯咯地响。“好,我们走吧。”他终于说。“到哪里去呀?”“跟我走好了。”“是到佳木斯去看电影吗?还是……”“同你说,不要多问了。”他有些不耐烦地揽过她的腰,重重地托了一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