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东清湾之惑
据1950年修订的县志记载,在1943年前后这一段时间里,东清湾村的青壮年(有少数女性),参加八路军的有九个,进入了A城绥靖军的有两人,而跟随张武备打游击的有六十八人,六十八人中,其中有六十四人死于最后的攻打A城的战斗。参加八路军的九个人当中,有三个活到了解放后,其中一个后来做了A城的第一任的市长,直到文革时被迫害致死;另外一个死在了朝鲜战场,他的墓碑至今仍在朝鲜江原道平康郡;而另一个,跟随大部队南下,后来留在了大西南,做过西南军区某师的政委。馁靖军中的两个人,在八路军攻打A城的战役中被击毙,他们的名字,没有人再提起过,他们的家人,在东清湾恢复声音后遭到了集体的镇压。而另外的六十四人,他们葬在了一起,他们死于同一个时刻。他们的灵魂,和一个叫做张武备的二十五岁的灵魂一起,仍然守候着东清湾,至今未变。
还有一些人,追随着平原上石匠们的脚印,投入了寻找一座山峰的队列中。到底有多少人加入到了那个行列中,没有人知道。他们到达过多少山峰,无人能够统计。而那个山峰是不是被他们找到,也无人知晓。1988年,几个来自上海的画家,深入到太行山区的腹地去写生,意外地发现了一座类似人形的山峰,远远的望去,山峰的顶端,隐约似一个人的脸,那张脸被浓密的树木掩盖着,不知经过了多少岁月的风霜。他们历经艰险爬到了山顶,再下到一个平台之上,他们才看到了一张脸,眼睛,鼻子和嘴,都有较为清晰的经过斧凿的痕迹。据说,那是石匠们未完成的杰作。而东清湾人直到2008年才组织全村的人去那里参观,位于大山深处的那座山仍然没有被唤醒,它仍旧沉睡在历史的尘埃中。他们无法像那几位画家那样冒险走到雕像面前,他们透过茂密的森林,站在对面的山上,远远的看着那座处女一样的山峰,内心涌动着不可言喻的复杂的情绪。没有人会去追究,那座雕像与现实中的张武备是否相似。东清湾的后人们,他们也在猜测,一段早已尘封的历史。
丁昭珂曾经努力想要跟随石匠们去探究一下他们非同寻常的举动。但是一旦要付诸实施,她才感觉到难度太大了,石匠们,不是一个系统性的组织,他们的行为,没有规律可循,他们完全是凭着一腔的热情。她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天真的想法,她不知道哪一个石匠能够到达最后的山峰,她同样不知道,他们需要多久,才能找到那样一座山峰。但是,当她返回A城时,她说到的一个人,却引起了我母亲张如清的注意。一个同样去寻找山峰的一个人,石匠,或者根本就是为了仅仅去寻找的一个人,他的样子酷似黄永年。丁昭珂所说的那个人的体貌特征与黄永年毫无二致。丁昭珂说,她当时还特意询问了一下那个年轻人,问他叫什么,家是哪里的,但那人笑而不答。我母亲急于要去印证丁昭珂的说法,她向二哥张武厉借几匹战马和士兵,和她一起去追赶那个人。这一次,张武厉倒是显得极为大度,他给了她一个五人的马队,他说,不消两天,你就能赶上那个人。但是,当我母亲迫切地跃上马准备启程时,张武厉说,也许你的命运和那些石匠们一样。她诧异地问二哥,什么命运?张武厉说,虚幻,缥缈。二哥的话并没有动摇母亲的决心,沿着丁昭珂所说的路线,他们星夜兼程,真的在第二天的傍晚时分赶上了那个年轻人。年轻人因为长途跋涉,正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歇息,他看着一队人马风风火火地来到他的身边,突然停了下来。我母亲只是看了那么一眼,就知道那个人不是黄永年,她失望的眼睛里有些湿润。随同而来的一个班长抡起马鞭要抽打年轻人时,母亲制止了他。那个失望的傍晚,母亲一句话也没说,都忘记了问那个年轻人的名字。他们临走时,给酷似黄永年的年轻人留下了一匹马。班长说:“你小子有福吧,就因为你这张嘴脸。”
母亲对黄永年的寻找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一年的夏末,从东清湾日军监狱,跑出来一个人,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是二哥张武厉。张武厉说:“是个中国人,姓黄,据说是两年前参与叛乱的一个学生。”母亲的心里立即想到了黄永年,即使不是他,也能从那个学生身上得到一点什么消息吧。在她的肯求下,张武厉才让她穿上军装,混进他的队伍里来到了东清湾,张武厉忧虑万分地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他们要血洗东清湾。”
他们赶到时,东清湾已经被日本兵围得水泄不通。同样来自A城的日本驻军独立步兵第二旅团的伊东正喜大佐,此时正骑在一头高头大马上,指挥若定。那些耀眼的黄色的服装像是一棵棵耀武扬威的树,种在东清湾的四周。张武厉告诫跟在他身边的妹妹张如清说:“寸步不离,知道吗,要和我寸步不离,否则没有人能保证你的安全。”我的母亲,那个最小号的军装穿在她的身上,仍然显得有些宽大,她惊惧地看着满眼的黄色,愕然地点了点头。那是冬天的东清湾,一些未知的命运在等待着它。
实际上,那是一次莫须有的搜捕行动。因为在若干天之后,当我的母亲回到A城,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眠时,黄永年的形象仍然停留在几年前,他来自己家参加父亲婚礼时的样子。我母亲想要再深入地从记忆深处打捞他的形象时,她意外地发现,已经变得十分困难,黄永年,越来越像是一个符号。而遥远的东清湾,似乎也已经归于死一般的寂静,只是恐惧,还在街巷里徘徊。
东清湾,衰败而死寂,军靴踏在地上的声音,异国的语言,使得母亲有种幻境之中的感觉。透过压得低低的帽檐,母亲眼中的东清湾,令人心碎地颤栗着。荷枪实弹的日军挨家挨户地搜索,想要找到他们所说的那个逃离监狱的黄姓男子。除了深藏于内心的语言,东清湾再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了,每家每户,几乎都是洞开的大门,搜查并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对了,还有,还有张洪儒,已经两年隐匿于黑暗屋子中的老人,他终于不得不重见天日,不得不再次地面对这个让他愧对的东清湾了。
这是那次搜查的终点,他们停在了张家大院里。伊东正喜与几个日本军官在窃窃私语,排成一行的日本兵把枪口对准了被钉得死死的石屋的房门。母亲听到了枪拴拉动的声音,挨着她的张武厉上前几步,和伊东正喜低语着,伊东正喜的脸色像是被铁铲子拍过,毫无表情。二哥无奈地退后几步,对着母亲眨了一下眼,摇了摇头。伊东正喜举起了手中的马刀,此时,拥挤的院子里突然人影闪动,一个人跑到了石屋前,用弱小的身躯护住了石屋的门,母亲惊讶地看着她,她的堂妹张彩虹。她把自己的身体摆成一个大字,毫无所惧地站在门前,眼睛瞪得大大的,没有一丝的恐惧。张彩虹的举动让举起马刀的伊东正喜很烦躁,他不得不放下手臂,走到张彩虹面前,对她说了句什么,语言对于张彩虹起不到任何作用,她站着那里一动也不动。军官的声调提高了八度,但是他的声音对于东清湾的人来说,有点太吵了。张彩虹仍旧无动于衷。提马刀的日本军官的声音已经无法再升高了,他的声音在东清湾的上空停留得很短暂,尖锐而刺耳。张武厉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母亲看到了二哥脸上的表情,她想要上前去把堂妹拉到一边,可是她的手被二哥张武厉紧紧地攥住了。二哥用目光阻止了她。日本军官的脸都憋紫了,他终于失去了耐性,他退回来,再次举起了马刀,然后快速地落了下来。有人发出了惊叫。张彩虹被被劈成了两半,她的脑袋和整个上半身,鲜血喷涌而出,把石屋的门染成了暗红色。她的两半身体,慢慢地萎顿下来,像是两件什么硬硬的东西掉到了地上。然后才是枪声,才是大门被打成稀烂的景象。大门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枪眼。枪声停止后,满身疮伤的门停顿了一下,然后突然一下子散开了,一个黑洞洞的世界出现在人们的眼前。那之后的世界对我的母亲来说,是红色的。她看到的一切,村庄,天空,树木,人,都是红色的。那是张彩虹的血,是她的血把母亲的世界染红了。张彩虹的血,不仅把母亲的世界染红了,东清湾,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都被那碎裂的红色所浸染着,就是二姥爷张洪儒,当他从被打破的门里走出来时,仿佛,莫测的黑暗还披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上也是红色的。他衣服的前襟,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红色。时隔两年,张洪儒仿佛出了一趟远门,他像是刚刚跋涉了很远的距离才回到了家乡,他站在门口,目光中满是茫然。他声音宏亮地问:“谁打扰了我?”院子里突然安静了一会儿,张彩妮的尖叫声也顿然消失了,我的母亲,张武厉,他们都把惊奇的目光投在了老人的脸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那张他们曾经熟悉的脸上,如今,那不是一张老人的脸,而是一张令他们完全感到震惊而陌生的脸,头发乌黑,面色红润,目光如炬,比他的兄弟张洪庭要年轻十几岁。有很多人想起了他把自己关在石屋前的样子,怯懦,苍老。我母亲张了张嘴,想要喊出“叔叔”那两个字,却没有发出来。那时,日本兵在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后已经悄悄地撤离了,院子里重新变得空旷了许多,张武厉也怀揣着对叔父的面貌的疑问,带领队伍返回了,我的母亲留在那里,她甚至忘记了脱下自己身上那套宽大的军服。张洪儒,他年轻的面庞留给大家的疑问会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如今,时间不允许东清湾过度地沉迷于此,还有更多的情感使他们变得慌乱和仓促。张彩虹的死,让悲伤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他们扑到了她的身边,暂时忘掉了一个老人相貌的变化,至于张洪儒是什么时候重新返回到石屋内的,至于他看到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来看望了张彩虹,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朵蒲公英,他们把它放在她的身体上,她被分成两半的身体,被厚厚的衣服包裹着,她的身上,被蒲公英覆盖着,像是夏季美丽的田野。张彩虹,躺在堂屋的一块床板上,她的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棉被,两半的脸被擦洗得很干净,张彩妮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她的两半脸,仍然无法正确地拼接到一起,有些错落。两边的嘴角都保持着上翘的姿势,像是一副知足安乐的模样,张彩妮,屡次想要把妹妹的嘴角抹平了,可没有办到。村里人觉得,棉被下面的张彩虹,在蒲公英的映衬下,娇艳而美丽,像是一个仙女。
三天之后的葬礼,没有如期举行,因为在那天夜里,张彩虹消失不见了。具体的时间可能永远是一个迷,大约是午夜时分,我的母亲发现床板上的薄被子塌了下去。她刚刚从一个梦境里醒来,梦里她看到了黄永年,他一会儿穿着日本兵的军服,端着机枪在扫射,他的脸上都是血,像是张彩虹身上绽开的血一样;一会儿他又变成了以前的模样,他对我母亲说,我爱革命。她冲到床板前,用手摸了摸,然后尖声叫道:“彩妮姐,彩妮姐。”张彩妮从身边缓缓地坐起来,她看着空空的床板,幽幽地说:“我看到她走了。”母亲着急地问:“她去哪儿?她怎么会走呢?”张彩妮摇摇头,“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儿。她把花儿都带走了,她是笑着走的。”按张彩妮的说法,她看到分成两半的张彩虹身披满身的蒲公英轻轻地飘了出去,蒲公英蓝莹莹,亮闪闪的,照着她的脸晶莹剔透。她是飞在半空中的,她的身体像蒲公英一样轻柔。她还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姐姐,向她招了招手。一到院子里,蒲公英就随风飘逝,飞向空中。张彩妮说,她分成两半的身体,一前一后,一左一右,一只手向姐姐招手,另一只做着同样的动作。她像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又像是一个人。张彩妮若有所思,“她可能变成了蒲公英,也让风吹走了。”我母亲回头再注意一下昏暗油灯下的床板,张彩妮说的一点也没错,满满一床板的蒲公英竟然一朵也不见了。我的母亲,不禁吸了一口凉气,她看着空空的床板,再看看悲伤的张彩妮,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似的。那个匪夷所思的夜晚,那个充满了蒲公英而又化为乌有的夜晚,悲伤似乎充满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它并不存在于人们的哭号之中,寂静和无声使张彩虹的消失似乎顺理成章。下半夜的母亲,再也无法入眠。她的脑子里,满是张彩虹的形象,她的形象突然之间就发生了变化,以前的那个羞涩而胆怯的姑娘,此时变成了两半人,两半人飘飘忽忽,一会儿是半张脸,一会儿又是毛茸茸的蒲公英。
关于张彩虹的神奇离去,还有两个说法需要补充一下,一是我的二姥爷张洪儒把她藏到了自己的石屋里,但是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当两年后他从石屋中走出来时,屋子里除了他头脑中子虚乌有的想法,空荡荡的;二是她的哥哥,游击队长张武备,在那个夜晚悄悄骑马返回了东清湾,用马载着妹妹离去,把她埋藏在了他曾经杀死过日本兵的地方。这个说法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是因为在不久后的未来,伊东正喜大佐被发现死在他自己的床上。死亡的方式与张彩虹的一模一样,刀砍,他被劈成了两半,鲜血染红了整张床。伊东正喜大佐的军刀,悬挂在床头,已经凝住的血把锋利的刀刃包裹住,看上去,军刀,像是一个玩具。A城的警报声一直持续到天明。日军、伪军、警察全部出动,他们几乎把A城翻了个底朝天,但是仍旧一无所获,寻找不到刺客的影子。令人惊奇的是,刺杀伊东的人是如何躲过了日军宪兵队重重的关卡的。伊东神秘的死亡被记在了张武备的身上,这给他传奇式的故事又增加了浓浓的一笔。这次在A城的传说把他形容成了一个会隐形、会飞檐走壁的侠客。
但是,张彩虹化成了蒲公英,这一说法渐渐地被大家所认可,因此,在我的家乡东清湾,蒲公英似乎特别地茂盛,在田野之中摇曳生姿,即使它的种子漫天飞舞,它也会留恋这块地方,他们说,那是因为张彩虹是蒲公英仙子,她不愿意到别处去。
在张彩虹化蒲公英而去的那个晚上,二姥爷张洪儒的石屋重新关上了,他变得年轻的面庞和身躯,只是短暂地出现在人们痛苦的回忆之中,而张武厉在返回A城的途中,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是什么使年迈的叔父返老还童呢?当他把看到的讲给自己的父亲说时,张洪庭一口断定,他自己的兄弟,在那个黑黑的屋子里研制什么返老还童丹。张武厉并不认可父亲的猜忌,他说,那是因为他把混乱的世界挡在了外面,心中没有了仇恨,没有了情感,心无旁骛,所以他才可以躲避衰老。
“胡扯。”姥爷说,“一派胡言。除非他死了。”
张武通若有所思地说:“爹。你不要不相信二弟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就像您说的那样,他把自己关在石屋子里,不见人,不见阳光,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自己无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真的是死了。如果他死了,当然他不会变老。”
姥爷愤恨地说:“真是无聊透顶,愚腐至极。”
实际上,关于我的二姥爷张洪儒如何变得年轻在东清湾一直是一个禁忌。张彩虹被刀劈的那天,张洪儒的意外现身,他变得年轻的模样,就像他本人一样,深藏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没有人去思考和讨论这样的问题,这仅仅是两年,三年,四年,十年呢,他会变成什么样?一个少年,或者婴儿吗?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东清湾,不需要答案。他们需要什么呢?
我母亲张如清离开东清湾时,是一个微风吹拂的午后,一朵蒲公英一直在跟随着她,在她的身前身后轻盈地舞蹈,母亲说,彩虹,如果你真的是彩虹,就请你替我把黄永年找回来。蒲公英,突然间告别了缠绵的舞蹈,直飞向空中,转眼间就不见了。母亲叹了口气,她不知道,她的寻找是不是还有意义。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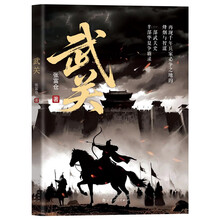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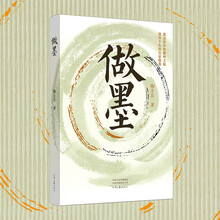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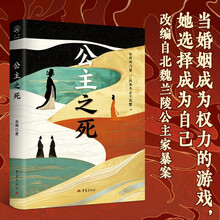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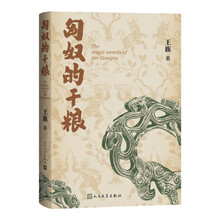



作为沧桑人世的物象,它矗立在历经战乱灾祸的大平原;作为刻骨铭心的文本,它定将不可摇撼地嵌入中国文学史。
——施战军(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