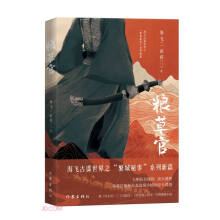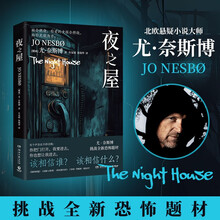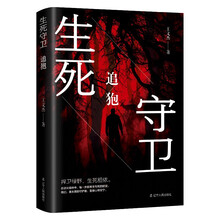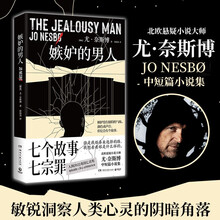然而,当真正扎根了农村我才知道,农民这口饭不是谁都能吃得了的,任你力气再大,膘子再厚,干一个月的农活一准儿会把你累得像扒了一层皮似的。好在不久之后,我就被村支书安排去打井队做帮手。本以为打井队的活会轻快些,没想到也是天天累得全身酸痛。
我落户的那个村子叫蒿岭村,周围水源充足,打井并不费事,因此我们打井队只有四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叫林海燕的女知青,一个打了半辈子井的老井匠和当地的一个叫牛二捶的小伙子。
老井匠全名叫马福贵,我们都叫他福贵叔。福贵叔家世代都是打井匠,对打井有独到的讲究,从选井定位到起井开掘都严谨得很。如果说打井是门学问,那福贵叔绝对称得上是位老学究。听福贵叔说,先前打井之时,一定要请阴阳先生拿着罗盘选准吉位,然后还要等到良辰吉时才能动土,否则打井就会不顺。
打井队唯一的女性林海燕是个性格开朗、甜美大方的女孩,父母曾经都是大学教师,她说起话来明显带着知识分子的味道,虽然不至于之乎者也的,但也经常好为人师。林海燕做事不喜欢输给别人,因此打井的时候,总是抢着干活,不怕苦不怕累,这一点一直让我非常佩服。
至于牛二捶则更是一个有趣的人,自从被安排到打井队之后,我索性卷了铺盖搬到了牛二捶家里与他同住。一来他爹娘现在都跟着他大哥大嫂,他自己独住一院,冷清得很。二来我俩都年轻,说话也投缘,他既没有农村小子的愣劲儿,我也没有城市小伙的傲气,两人一见面就像发小似的热络起来。晚上我俩时常会聊到半夜,说至兴奋处,甚至连白天的疲乏都忘了。那时候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对自己、对未来、对人生充满了斗志,浑身洋溢着“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气概。
那年头都缺吃的,半夜饿醒的事是常态,二捶这时候就会拉我去抓麻雀回来烤着吃。不要以为晚上抓麻雀是天方夜谭,其实晚上去抓麻雀才是最适当的时机。牛二捶的方法通常是先是找一棵繁茂的杨树,然后脱了鞋顺着树干爬上去。麻雀这东西,别看白天古灵精怪的,一到晚上不仅眼神不好,胆子也变小了,就算听到什么动静,也不敢随便轻举妄动,非等到被人攥到手里了,才扑棱着翅膀想飞,但这时哪还来得及,一下就被塞进了黑布袋中。牛二捶用这法子抓到过不少麻雀,但他也有原则,一旦抓到幼雀,就会毫不犹豫地放走,他说这是历代的规矩,不吃幼雀,吃了会遭报应。
就这样我们四人组成了蒿岭村的打井队,平日里我们东奔西走,哪里缺水就去哪里打井,有时还会被调到别的村子去。那时生产力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只能靠人工打井,而打井是个技术活,不是随便一挖就能挖出水来,这得需要井匠先定位,然后再进行“起井”。以前井匠在农村算得上是体面的手艺人,一辈辈的人全指着打井吃饭,因此其中的诀窍从不轻易外传。这使得井匠成了个稀罕人物,七里八乡的往往只有一两户井匠。
“井匠世家”出身的福贵叔自然是我们打井队的中坚力量,除了下井挖土,打井的其他工序全指着他。现在大家都吃大锅饭,谁也饿不着,福贵叔也不担心有人会抢了他的饭碗,因此一空闲了,就会跟我们絮叨打井的窍门,例如选井位,讲究看地表上花草的种类,如果地表上长的是冬青、落地生根。观音莲等不喜水的植物,那么下面就很难打到水,即便是能打到水,井筒子也势必要往深里挖了。而如果地表长的是蒿草、竹子、铜钱草这些喜水的植物,那就绝对不愁打不上水来。
对于福贵叔的这些选井诀窍,我们闲来无事也就听听,不过我们还是最喜欢听他说起他祖辈历来的一些离奇的打井经历,像是他的爷爷曾经在打井的时候挖到过一只能让井水冒泡的翡翠蛙。他的老爹马老汉则挖到过一座两米多高的龙王爷石像。福贵叔也挖到过稀奇古怪的东西,不过他的运气并不怎么好,挖到的是一坛腌了不知上百年还是上千年的咸鸭蛋。
对于福贵叔说的这些事儿,我和牛二捶听着也就图个热闹,并不当真。如果打井真能常常挖到宝贝,我们干脆改行做考古得了,努努劲儿从地里多挖出些金银珠宝、翡翠玉石,让广大人民群众人手一堆,那我们眨眼就步入小康社会了。
然而,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年立春刚过,正是小麦拔节,柳树抽芽的时候,我们接到了村支书的指派,去附近的余家寨帮他们打一口井。这一次,我们真就挖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
一听去余家寨,我和二捶就开始叫苦不迭。这余家寨处在附近天台山的山腰上,是远近闻名的缺水村。几百年来,村子里为了能打一眼有水的井,费的粮食钱财不计其数,可就愣是没打出一滴水来。村子里的人吃水得走十几里的山路下山挑水,其艰苦程度自不必说。现在单单就让我们四人去攻克这个难关,实在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