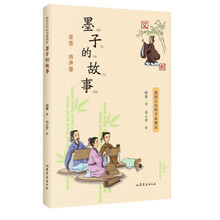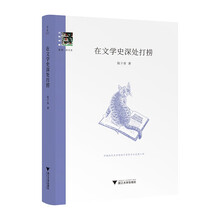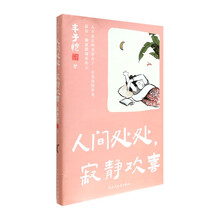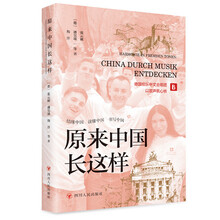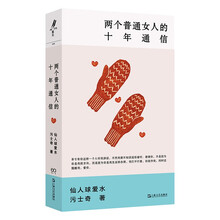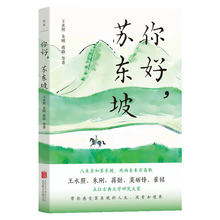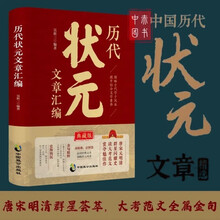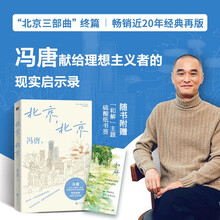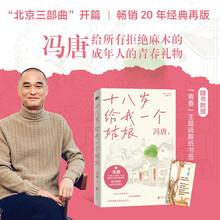经这一番不落俗套的铺陈,海棠花立时有了声音的色彩,在本是恬静的千朵万朵花丛中,唱起了春之歌,回响起海的涛声,把一般赏花人视为静止的花赋予跃动的生命力。这里,诗人没有写花的形状和香味,但读者仿佛和千万赏花者一同在花潮中荡漾,看到繁花似锦,闻到花海腾香。这种化平凡为神奇的艺术功力,令人击节赞赏。文章从开头写到这里,区区六百字,写了花的色彩、花的景致、花的潮声,由色入景,由景入声,丝丝相连。可以说,如此描绘海棠花可谓达到了穷形尽态的境地。读来一气呵成,又从容舒展。这俨然是一帧艳丽、婀娜的海棠花会图。
但是,文章如果有景而无情,或景浓而情寡,那就索然无味了。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中说:“情者文之经”,“为情而造文”。写真景,抒真情,创造一种贮满诗情的艺术境界,才能把读者引入佳境,牵动读者的情思。《花潮》在写花咏物时,虽也曾倾注了诗情,但作者笔端凝聚的浓郁的感情,主要还是倾注在写赏花人上面。他用一半多的篇幅写人们如何在树下花间看花,“这棵树下看看,好,那棵树下看看,也好,伫立在另一棵树下仔细端详一番,更好,看看,想想,再看看,再想想”。人们在花下“一步千徘徊”,不忍离去。男女老少,徜徉在花海中,如痴如醉:扶着拐杖的老妈妈,竟情不自禁地折下一朵插在鬓发;穿红着绿、点胭脂、抹口红的姑娘少妇,欲与花争妍,“显得很突出”,那些带弹弓来射鸟的孩子们也被花“惊呆了”;画家和摄影的人们,更是目不暇接,不知要画花,还是要照人;连娇艳的茶花,俏丽的梅花,妖娆的桃花,旖旎的滇池,丰腆的平林和原野,在海棠花事面前,都黯然失色,无人问津。这样一写,不仅进一步烘托了“花潮”,而且写了人潮,潮潮相激,在读者心里涌起层层心潮。这因写花而写人,写人对于大自然的质朴的感情,表现了李广田散文一贯的风格,但却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李广田早年的散文,如《山之子》等,有一种对大自然和故乡的朴实的感情,但有时不免带着淡淡的忧郁情调。而《花潮》却感情浓烈,色彩斑斓,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已成了生活的主人,大自然的主人,他们不再为生计忧虑、奔波,劳作之余,尽情游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