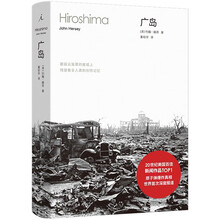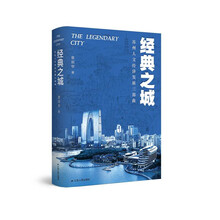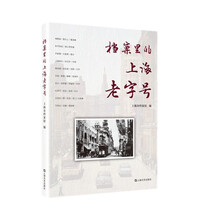到星期四上午,镇上几乎无人不知“小鸭子”回家了——或者说快要回家了。上午,家属们陆续到达。他们是:哥哥,赫谢尔,人们都叫他“大鸭子”;妹妹,贝蒂?乔;还有吉布森的妻子,卡罗琳。他们伫立于装在玻璃罩中的遗体周围,任凭眼泪洒落在玻璃上。人们站在隔壁的加油站和外面街道上,轻声交谈着。士兵的双亲,诺曼?吉布森夫妇,在家等候。他们家是一幢匀称的白色房子。位于山谷之中,可以远眺几英里以外的费拉克斯?帕奇河。吉布森太太这月来一直生病,家人不让她动身前往欣迪曼。临近晌午,“小鸭子”被放人灵车运回家,一路上山谷的闷令人窒息。梅吉?莱尔?霍尔德曼助理军官是一名越战幸存者。他同里特上士一样被派来慰问死者家属,他也加入了送灵的队伍。这支队伍缓慢地走过一段长长的路程——翻过一座高高的山脊向南,沿艾丽斯曼河而行,途经安布尔奇小镇。在安布尔奇,当灵车穿过人群时,当地人站在烈日下,女人们哭了,男人们纷纷脱帽。邮局局长诺拉?安布尔奇夫人在当地四等邮局下半旗志哀。她说:“我们都认为‘小鸭子’是个好小伙子。” 在费拉克斯?帕奇河与艾丽丝曼河汇流处,灵车拐弯。驶过一座小桥,沿艾丽丝曼河顺流而上,这里离吉布森家还有最后一英里路程。死者父母和其他亲戚默不作声地在昏暗的家中等待着。当棺枢抬进门廊,穿过大门来到起居室时,悲怆的哭喊声划破静寂。凄惨的声音一声高过一声,传向山谷。“小鸭子”回家了。整个下午直至深夜,人们络绎不绝。有步行来的,有乘各种车辆驶过满是尘土的山路前来的。人们带来了鲜花和食品。到后来,起居室里摆满了花圈,厨房摆满了食品。满屋满院都是人。死者家属悲痛地和前来吊唁的人们一一握手。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走过去凝望棺材里的死者,泪流满面。死者的母亲是一位面目慈祥的山区妇女。灰白色头发梳在脑后结成一个发髻。她拖着病躯,神情恍惚地走进人群说:“无论怎样,他的遗愿一定会实现。” 死者的父亲是个高而黝黑的汉子,两眼哭得通红。他说:“他并不想当兵,但他知道当兵没错,因此他努力干。他献出了一切。我真为他感到自豪。现在,他们就这样把他送回家了。” 午夜时分,又下起了暴雨。吊唁的人们聚到屋子里,走廊上。还有人站在屋檐下的墙边。父亲轻声讲述着他的儿子。“大概诸位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叫他‘小鸭子’吧?在我两个儿子小的时候,他们一有机会就去河里玩水。于是有人说他们像两只鸭子。” “从那时起,赫谢尔成了‘大鸭子’,詹姆斯成了‘小鸭子’。” “人的一辈子总是在拼命干活以养家活口。我在一个煤矿干活,趴在坑道里装煤供养全家。” “我们全家人亲密和睦。小鸭子就生在这里,在这幢房子里。他从没想过离开。” 吊唁的人们走上前去,纷纷赞美“小鸭子”。“他从不酗酒,从不在夜里顺着公路来回跑。” “他关心家庭,是个好孩子。” “小鸭子”身材高大魁梧,体重205磅。他的块头使他成为高中校篮球队的一员。在康斯高中,他结识一位女孩并向她求婚。他们今年一月举行了婚礼。“小鸭子”最近曾回国休假。在他顺费拉克斯?帕奇河而下归队后一个月,他又回来了——他将被埋葬在故乡。部队说他在西贡附近被迫击炮弹片击中,但死亡详情无从知晓。凌晨,一片静谧。死者父亲回忆起儿子归队的那一天。“他到处走来走去,样样东西都看看。他对我说:‘天啊!回家实在太棒了。”’ “然后,他就上路了。他说:‘爸爸,注意身体,别操劳过度。”’ “他说:‘我下次回来看你。’但他现在不可能看见我了。” 一位老者威严地迈着步子走到前面说:“没人说‘小鸭子’坏话。他是你们所见到的最好的孩子。” 起居室内充满花香。“小鸭子”母亲悲切地坐在儿子身旁。她的一只手微微前伸,像是抚慰一个陌生人。她像在自言自语:“为什么,我的孩子?为什么,孩子?” 她望着覆盖国旗的棺材。突然转过身来说:“只有亲眼看见一面国旗盖在你自己儿子的身上时,你才会懂得它的含义。”说完又转过身,对着棺材哭泣不止。星期五下午,“小鸭子”被运到普罗维登斯宗教浸礼会,安放在布道坛后面。教堂的灯亮了一个通宵。人们陪着死者,不停地祈祷。死者父母在浸礼会整整呆了一夜。“小鸭子”母亲说:“这是他最后一个夜晚。”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