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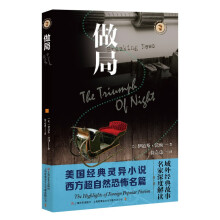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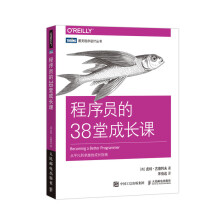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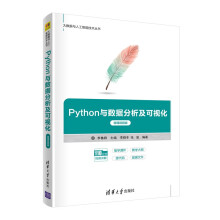



如果你想读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本书会让你失望;但是,如果你想从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中感悟婚姻的真谛,本书就是你的不二之选。
一个才貌双全的女人嫁给一个勤劳能干却并不成功的工程师,经历了新奇、幻想、失望、兴奋与无奈,也经历了外遇、激情、丧女与婚姻冷战,遍尝婚姻酸甜苦辣的滋味。最终,她悟出:所谓婚姻,其实就是一个安息角。
安息角是建筑学上的词汇,指一堆散料保持自然稳定状态的很大角度。一旦这个角度形成后,再往上堆加散料,就会自然滑下,并保持这个角度。同理,人们只有找到了安息角,才能让婚姻保持稳定。每个稳定的婚姻都是因为找到了安息角,每个不稳定的婚姻都是因为还没有寻找到安息角。
《安息角》中的故事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状态,让人反思,令人憬悟——不论你是女人还是男人。
4.2
天刚蒙蒙亮,火车还在空旷的平原上隆隆轰鸣,她就早早地把自己的东西聚在了一起。过了好久,火车才缓缓驶入铁路棚车之间,一声嘶鸣后停在了在丹佛车站的月台前。她迫不及待地紧随搬运工朝车门走去。车门一打开,她两眼不停地东张西望,在人群中寻觅他的身影。
然后她看到了他。他并没挤在人堆里推来搡去,而是站在车站壁角,鹤立鸡群地环顾着众人。她脑海里跳出的头一个念头就是,以后不能再叫他“小家伙”了。他脸孔明显消瘦下去,皮肤看上去也是饱经风霜,只有他扭头时才能看到脖子处刚剪过的头发后有一圈粉嫩的肌肤。他双目高举,面无表情地挨个检视着各行其是的乘客,淡漠得就像是在等一趟货车,而不是一年多没见的妻子。
他和她分开了这么久,居然对她的到来表现得如此冷漠?他是不是还在怪她闹得夫妻分离,其实她也一直为此责怪自己;还是他觉得她脑袋里哪条筋搭错了,硬要跑来他身边和他过?虽说他现在脚跟站得稳些了,但要说让她来利德维尔生活,恐怕还不到时候。
她觉得他总是提防着别人,把自己的想法闷在心里,但做起事来又都顺着别人的意思。
然后那双漠然的眼睛发现了她。他眼神里的变化让她难以遏制地兴奋起来,用力挥舞起手中的黑手套。隔着四十英尺的喧闹,两人傻傻地相视而笑。他走过来,她迎上去,牢牢揽住他,任他一把抱起。他说:“啊,苏珊,终于把你给盼来了!我真怕你又是说说而已。”
“我怎么能老对你说话不算数呢。你看你都瘦成这样了!你还好吗?”
“好得不能再好了。但在这种海拔,还有克拉伦登的饭菜,想胖都胖不了。”他抱着她仔细打量,又说,“你也瘦了。一路上还顺利吗?奥利怎么样?”
“我很好,”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路上也很好。列车员还请我到火车头去坐坐呢,不过我没去。奥利好多了,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抛下他自个儿走了,我真不是个称职的妈妈。”
“你少来啦。”
“我的确不是好妈妈嘛!”她的情绪有些失控。
“怎么会呢?”他笑着说。
“哦,是不是还蛮讽刺的?”苏珊大声说,“我之所以不肯带他去枯木镇,是怕他住在简陋的营地里会生病,到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去找谁。所以我才带他回米尔顿的,可没想到他却染上了米尔顿高发的疟疾。我从来都没这样寂寞过。上个月的事,实在是对不住。
我正准备过来的时候,他却病了。我难过极了,于是就让韦尔先生替我给你发了电报。他和我同一班火车来的西部,我觉得这人还靠得住。”
“他这样都叫靠得住?好吧,”奥利弗说,“他一直到芝加哥才发电报,他大概是想帮我省个一块钱吧。那时我已经离开利德维尔来接你了。他替我省下了一块钱,结果浪费了我两百块,还害得我站在月台上,冻得上牙打下牙。我在车站足足等了你三天,才收到了弗兰克的消息。我在回山里的路上,心里直骂那个该死的韦尔先生。”
“啊,现在好了,”她握着他的大手摇来晃去,说道,“现在我们可以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就像第一次去新阿尔马登的新家那样。”
他溺爱而包容地看着她,她看得出她的一言一行都叫他着迷。
“哦,别想得太美了,”他说,“回家的路不好走,我怕你会叫苦连天直埋怨我呢。”
“那到家后呢?”
“到家后,我立即跃升为利德维尔两个最令人羡慕的幸运儿之一。霍勒斯·泰伯呢,是那里最有钱的人;而我呢,是唯一有家主婆的男人。”
“不会吧?那儿就没别的女人啦?”
“女人是有的。可称不上是‘家主婆’。都是些寡妇啦,她们自己说的,还有就是些出租屋的女老板,还有几个婆娘跟男人似的,穿着裤子,成天妄想要下矿挖洞。嗯,兴许有一个还能叫做‘家主婆’的,不过经不住她德国男人的拳打脚踢,逃到蚊子关去了。”
“老天呀,”她故作惊恐地说,“听起来你这一年过得很热闹啊。”
“记住啊,你只许跟我一个人说话。”
“你看你这个小气劲儿。”
“随便你怎么说。”他没有放开她的手臂,缓慢地摇动着她的肩膀。她又看见了他那久违的笑容。当初的微笑是何等温暖,她差不多都忘光了。他消瘦的脸颊,加深了眼角的鱼尾纹。月台上的人群渐渐疏散。任凭四周风沙漫天、纸屑飞舞,他俩的眼里却只有对方。
搬运工把她的行李提了过来,放在他们身边几英尺处。奥利弗放开她,摸出一个银元当小费,随后一手提起一个包,用左肩护住她带起路来。“和我讲讲蚊子关吧,”她说,“是不是像《莱斯利画报》里登的那样吓人?死马、破车、恐怖的悬崖?”
他赞同地说:“确实挺吓人的,不过呢,也不至于吓成德国家主婆和画报记者那样。”
“为什么呀?”
“首先,我不会对你拳脚相加。其次嘛,你也知道,画报把西部画得那么恐怖,不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你们这些东部人吗?”
她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在丹佛住上一晚。可他们连坐下来好好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要去赶乘丹佛-南方公园-太平洋窄轨去费尔普莱,不到一小时就要发车了。就是等午餐外卖耽搁了些时间,差点就误了车。等他们气喘吁吁地上了火车,只剩下一个空座位了,还是坏的。奥利弗将外套铺在座位上,又用苏珊的毯制旅行袋支在下面,让苏珊坐下。她夹在奥利弗和窗口间东倒西歪,连三明治都送不到嘴里。
“这真像是一次冒险。”她说。
“嗯。”
“火车开过圣达菲后,显得那么渺小。如果现在要画我们,得从高处往下取景,把我们的车画成消逝在大山间的玩具小火车。”
“以后再说吧,”奥利弗说,“我们到达‘斯莱克斯’与队伍会合后,山会更加高大,我们小得连影都瞧不见了。”
“斯莱克斯”位于钢铁厂的末端,一冲沟的窝棚、帐篷和矿车,丑陋得像块赘肉。一群汉子正将从莱德维尔冶炼厂运来的三大矿车精砂装上平车。
奥利弗抱起苏珊趟过泥地,将她放在一堆枕木上,然后又继续走向更深的泥地,上街去取前天留在那里的马车。他一边走着,一边不时地扭头看她,还两次从马厩门里看她是不是独自一人等在原地。周围的人们注目观望着她,看着他驾车回来,将她的行李和包裹放上车,把她拉上座位,将野牛皮衣铺在她脚下,又在她膝盖上覆上灰色毛毯,然后动身驶向基诺沙关。
“这儿不是有辆公共马车吗?”她问道,“又便宜又省事。”
“有是有,不过不是‘爱妻号’。”
虽然已近 5 点,但日光依然跟大白天似的热辣辣地晒在他们的脸上。道路一段是泥土、一段是乱石,然后又是泥土,好不容易过去了又碰上了脏脏的积雪。接着,马车倾斜着滑向小溪,幸好马儿被皮带拉牢,奥利弗的手带住了刹车拉闸,峡谷壁的阴影压倒过来,一阵寒意袭上他们的身体。
在黄昏的凉意中,她望着路途中奄奄一息的病马,载满货物、陷入瘫痪的马车,以及专心致志赶车的奥利弗,突然感到了内心的渺小、忐忑和依赖。她拉过毯子裹在身上,挨近他的身边,尽量不去妨碍他驾车。他将缰绳都握在左手,右手揽着她,两人俨然一对浪迹天涯的眷侣。
“累了吧?”
“从我早上起来,好像已经走了很久很久了。”
“我了解。再来个香喷喷的三明治,如何?”
他们一边吃一边爬着昏暗的冲沟。只听奥利弗说:“留神,抓稳了,前头有辆公共马车。”
在奇特的粉红暮色中,公共马车费力地攀爬着他们前面的斜坡,看起来像是从童话世界里跑出来的。上面全是男人,至少有七八个。“地方挤挤总会有的,”奥利弗说,“我们上吧。”
他扬起鞭子抽打马儿,将马车拉到公共马车近旁。两车相距不足10英尺,车上的男人们纷纷居高临下地俯视起苏珊的马车来。整辆车弥漫着一股威士忌的气味,夹带着马车自身的气味,移动前行。上面的男人们紧盯着她不放,显然怀疑粉红的暮色花了他们的眼。他们嘴里放肆了几句,她充耳不闻,任马儿拉着驶过他们身边。
然后两车齐头并进起来。那车夫在颠簸中稳坐如山,驾轻就熟地把持着缰绳。他看了过来,愉快地把头一点以示问候,张开了嘴。而这时,奥利弗也勒住缰绳,不再往前赶,与那车夫颠簸着并驾齐驱。那马车夫高兴地喊道:“嘿,沃德先生!今天晚上有没有兴致到老妪岔口游游泳?”
“丹尼斯,”奥利弗应道,“是你吗?你跑到利德维尔的道上干什么?不会是迷路了吧?”
“那别人上这儿干什么来的?”丹尼斯说,“你自个儿呢?”
“带我老婆回家呢。”
“嗯?”在几近黑暗的光线中他的眼睛触碰到了苏珊的双眼,她挤出一丝笑容。他一时失语。而旁边车上的乘客们,不约而同地透过窗户望过来,兴致盎然地倾听着他们的对话。山峦间蓝天寥廓,峡谷的深渊青黑如黛。马车走得跌跌撞撞,她抓紧挡泥板后,奥利弗举起鞭子向朋友告别,然后快马加鞭地越过山头。疾行了一刻钟后,已将那辆公共马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那个是谁呢?”看他似乎没打算主动告诉她,苏珊只好开口问。
“丹尼斯·麦奎尔。去年春天他在夏延到枯木镇这段赶公共马车,四天的路程,他的马车竟然要走 13 天,出了名地慢。”
“他那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到老妪岔口游游泳啊?”
“我们之前不是被洪水困住了。我没在信里和你说起吗?”
“你给我的信里面从来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你只是说,路上的时间很长,也不说为什么。”
“我们在那里困了两天,指望着河水能退下去,可雨就是下个不停,结果水越积越深。最后,我和一个叫蒙大纳的老兄决定碰碰运气,赶着马车趟过去。其他人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只好让我们去试试。谁知这六匹马一下水就游开了。你问我冷不冷?噢,我的天。我回头一看,那部老爷马车跟水漫金山似的,里面的人争先恐后地往车顶爬,就像粮仓烧着了,老鼠一窝蜂似的逃出来。真是乱作一团。”
“但你还是成功了。”
“哪儿有,”他说,“我差一点就英年早逝了。奥利弗·沃德,溺水身亡,尸骨无存。”
“还好你没把这事写进信里,谢天谢地。”她说,“我这人最怕死了。”
“你总是一惊一乍的,其实啥事都没有。”
“还要走多久?”
“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费尔普莱了。”
他一手揽着她,一手驾车。马匹脚如注铅,坚忍地向前迈步。
他们跋涉在乌漆墨黑的道上,在野生植物群中游荡了一阵。绕过防风林后,一下子进到了另一个世界,灯光和声音劈头盖脸地扑过来。街上的人还真不少。隔个三道门就有间酒馆,将灯光大面积地投在泥地突起的木板人行道上。在嘈杂喧嚣中,她听到了钢琴的声音。大门敞开着,传来男人们阵阵的低沉吵嚷。
奥利弗惊叹道:“哇。”他高举提灯,照射着起伏的原木墙面和茅草屋檐。他把缰绳塞到她手中,吩咐说:“待在这儿别走开。”然后重重地跃下车去。她高高坐着,听着城市街头在她背后喧嚣,还有一些牲畜的响动,不知是从哪里的畜栏传来的。
一扇门在一盏提灯的照射下吱呀开了,另一盏提灯照面晃过来,照出移动的双腿。有匹马长吁了一声,就像她自己舒了一口气。
小马倌将马匹从马车上解开,牵走了马队。奥利弗扶苏珊下了马车,拖着袋子走在她身后,把提灯递向她,问:“你拿着好吗?”
“当然。”
“再有一点点路就到旅馆了。”
灯光将盆栽棕榈的阴影投在木板上,还照出屋里的戴帽的男人们,就在此处赫然挂着一个招牌,上头写着“旅馆”两个大字。他领她走了进去。屋子里烟雾腾腾的,墙上挂着面美国国旗,六个男人正坐在椅子里抽烟,其余的人都在隔壁房间的酒吧,黄铜痰盂泛着圆润的光泽。
对角的柜台后,一个戴着条纹束袖带的年轻人站起来,放下报纸。他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苏珊,说道:“对不起,老兄。客满了。”
“我预定过的。”奥利弗说,“我前天来过,预定了间双人房。我付了五块钱定金,住宿登记簿上也签了名。”
奥利弗拿起登记簿翻起来。突然他翻回一页。在他手肘下方,苏珊看到了他的名字,熟悉的笔迹上被铅笔划了道杠。奥利弗说:
“就是这个,哪个把它划掉了?”
“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伙计说,“我只知道,我们一张单人床都没有了。”
“这里还有出租屋,”他说,“我可以让这孩子去看看有没有床位。”
“不用麻烦了,”奥利弗说,“是在哪儿?”
“就在左边的街区。你看,沃德先生,让小孩子跑跑腿没关系,你两口子先坐下歇会儿。”
“把那五块钱定金退给我,这事就算了。”
他话音刚落,那伙计立马打开抽屉,取出五块钱来,动作神速得让她惊讶。他把钱放在奥利弗的手中,又道了一次歉。
他们来到街角,朝左拐了个弯,找到了出租屋。一名身穿汗衫的男子正坐着喝咖啡,说他们还有床位,不过床和床之间只隔着层帘子,好像不太适合这位小姐。奥利弗看了她一眼,要下了这张床。汗衫男拿起灯,带他们上楼后沿着大厅朝前走。四壁都是蓝色壁纱帘,他们走过时带起一缕微风,拂动轻纱帏幔翩翩舞动。三人来到一扇不带锁的门前。苏珊走进去,在床上坐下,发现这间房也没有墙壁--只在离地六英尺的架子上钉着蓝色纱幔,将屋子隔出一个个十英尺长、八英尺宽的小间,还被冷风吹得瑟瑟发抖。周围的鼾声一清二楚。这地方冰冷冰冷的,冷得可以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
奥利弗跪在床边抱住她,嘴唇贴在她冰冷的面孔上,连声说着“对不起”。
“没有关系。我什么地方都能睡。”
“真希望我们已经到家了。”
“是呀。”
“在这个鬼地方,我们连话都不能说。”
“留到明天晚上说不也一样。”
……
“大师级的著作。阅读它是一次值得珍惜的宝贵经历。”
——《波士顿环球时报》
“斯泰格纳呈现的不只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道华丽的语言大餐,每个词语、每个句子都吸引着你的眼球,让你无法快速掠过任何一处。”
——《洛杉矶时报》
“斯泰格纳的《安息角》是一部精品小说,一本关于婚姻和婚姻本身的严肃小说。”
—— 伊丽莎白·亨得利
“《安息角》是对婚姻的诠释,它帮我们找到了维护婚姻生活的很好点。”
—— 佩吉·文森特
“这是一个伟大的西部故事,西部的神奇完全在本书中得到体现。同时,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人性的脆弱、爱和宽恕的力量。更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还引起了女权作家的争论。不管怎样,这部小说依然是20世纪后期写得很好的一部西部小说。”
—— 罗伯特·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