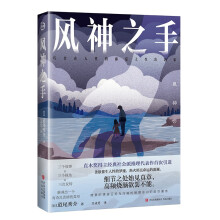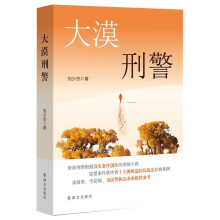“他真该死。穿着靴子上床吗?”
“是的。”
神秘的事情对汤姆·莎耶真是无价之宝。你要是把一件神秘事、一块糖面饼放在我和他的面前,你用不到再要我们选择;一切早就安排定当了。因为我的天性总是跟了糖面饼走,他的天性总是跟了神秘事走。人人生来不一样。这原是最好的办法。汤姆和那个侍者说: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菲力浦。”
“他在哪儿上船的?”
“我想他是在衣阿华那头的亚历山大里亚上的船。”
“你觉得他在搞些什么玩意儿?”
“我一点看不出——我从没有注意。”
我自己对自己说,这儿又是一位跟了糖面饼走的。
“他的动作和说话的样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没有,他只是看上去十分担惊害怕,一天到晚把房门锁着,你要是打门,他总是先掀开了—条缝,看清楚了是谁,才让你进去。”
“他妈的,真有趣!我实在想看他一看。我说,你下次再到他房里去,你想你能不能把门开直了让——”
“那没用!他总是站在门背后。他会把它挡住。”
汤姆捉摸了半天,然后说:
“我对你讲。你把你的围身借给我,早上让我来给他送早点。我给你两毛半钱。”
那侍者非常愿意,他只怕领班不答应。汤姆说那不要紧,他自有办法去安排那个领班。他安排得很圆满。我们两个人可以系上围身,带着杯盘,一同进去。
他没有睡好,心里急于想走进那个房间去察看菲力浦的神秘;他一整夜左猜右猜地猜个不停,这根本没有用处,因为你既然准备直接去发现事实,那又何必胡思乱想来消耗精神?我一睡就着。菲力浦究竟搞些什么鬼不管我的事,我自己对自己说。
一大早我们系上围身,捧了两盘点心,汤姆在房门上叩了几下。那人掀开了一条缝,然后让我们进去,立刻又把门关上。我的天哪,我们一见到他,差一点把盘子都摔在地上!汤姆就说:
“咦,木星·邓莱普,你打哪儿来的?”
那个人当然吓了一大跳;他起初好像不知道自己是惊是喜,还是又惊又喜,还是怎么的,可是后来决定应该高兴;脸色也逐渐恢复,虽然早先变得白极了。他一边吃早饭,我们就一边聊起天来。他说:
“我并不是木星·邓莱普。我可愿意对你们说明我是什么人,你们千万不能讲出来,我根本也不姓菲力浦。”
汤姆说:
“我们决不会讲的,可是你如果不是木星·邓莱普,你就也不用说你是谁了。”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不是他,你就是那个双生弟兄。你和木星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
“不错,我是杰克。再说,你怎么会认识我们邓莱普家的r’
汤姆就把去年夏天我们在他赛拉姨父家里那些历险的事情告诉了他,他一看他家里的事情——连他自己的事情也在内——没有一件我们不知道,他就放下了心,谈起话来也十分自由和坦白了。他关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也不隐瞒;他说他一直是个亡命之徒,现在还是个亡命之徒,也许到死仍旧是个亡命之徒。他说这当然是一种危险的生涯——
他忽然屏住了气,侧着头在倾听似的。我们都不说话。所以有一两秒钟静极了,外面除了木板的咯吱声、机器的轧轧声以外,一些没有别的动静。
我们随后又使他安定下来,讲些他自己家里人的事情给他听,布雷斯的老婆怎么样已经死了三年,布雷斯怎么样想去娶蓓妮碰了一鼻子灰,木星怎么样在替赛拉姨父帮工,他和赛拉又怎么样一天到晚拌嘴——听到这儿,他情不自禁,就哈哈大笑起来。
“咳!”他说,“听你这样说长道短,我好像又回到了往年的日子里,我心里真舒服。我已经有七年多没有听到一句这类的话了。他们平时讲起我来说些什么?”
“谁?”
“那些庄稼人——和我家里的人。”
“他们根本不讲起你——至多难得提一句。”
“他妈的!”他诧异地说,“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都以为你早就死了。”
“不!你说的是实话吗?——你对天起个誓。”他兴奋得跳起身来。
“我对天起誓。他们没有一个人以为你还活着。”
“那么我得救了,我当真得救了!我可以回家了。他们可以把我藏起来,搭救我的性命。你们切不可讲出来。你们得赌个咒说你们决不讲出来——赌个咒说你们决不出卖我。啊,孩子们,可怜可怜我这个苦命鬼,日日夜夜让人在后面追赶,吓得我不敢抛头露面!我从来没有损害过你们,皇天在上,我永远不会损害你们。赌个咒说你们肯可怜我,搭救我的性命。”
他哪怕是条狗,我们也肯为他赌咒;我们于是赌了个咒。他对我们真是说不出的亲热和感激,千恩万谢的,差一点儿要搂住了我们亲嘴。 我们一路聊下去,他拿出了一只小小的手提箱,开了开来,又叫我们把脸背过去。我们依他做了,等他叫我们转回身来,他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子。他戴上了一副蓝玻璃的避风镜,又有一脸棕黄的长须,简直像真的一样。他自己的亲妈也不会认得出他。他问我们,现在像不像他的兄弟木星了。
“不像,”汤姆说,“除了长头发以外,什么也不像他了。”
“好吧,我到那儿以前,一定把它剪短;他和布雷斯会替我保守秘密,我就装作是一个陌生人去和他们住在一块儿,邻居们再也不会猜得出是我。你们觉得怎么样?”
汤姆考虑了一会儿,就说:
“当然我和哈克是决不会讲出来的,可是你如果自己跟人讲了,那就有些危险——也许不大,可是多少有一点儿。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跟人谈话,他们会不会听出你的声音和木星的十分相像;会不会想到他们以为死了好久的那个双生兄弟,不过是化了名一直躲藏在什么地方?”
“天哪,”他说,“你真聪明!你说得对极了。有邻居在边上的时候,我只能装做聋子和哑巴。咳,如果我一口气奔回家,没想到注意这种小地方,那可糟了。可是我并不预备一口气奔回家,半路上我就要溜走,让那些追踪我的人可以找不到我;然后我化好了装,再去买些衣服来换上,再——”
他忽然跳到门边,把耳朵凑在上面倾听,脸又白、气又急,隔了一忽,轻轻地说:
“好像是扳枪机的声音!天哪,这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他于是倒在椅子里,浑身瘫软好像得了重病,又用手把脸上的汗水抹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