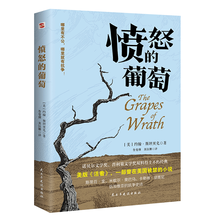默赫许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改卷子。一列火车急匆匆地呼啸而过,身后拖着柴油的味道,铁轨的震动声还在空气中回荡,默赫许抬起头,看了看窗户的拱顶。秋天带着它的湿冷和沉闷,像一个有着必然结果的命题,稳稳地在屋里扎下根来。这是他在英国度过的第十一个秋天,也是在这间办公室里度过的第四个。默赫许再次抬起头。墙上贴着各式表格和图片,从他所在的位置看去,世界地图挂在一个十分别扭的角度,蓝色的海洋刚好被铁书架挡住。书排得满满当当,中间还夹着论文和其他文件,橙色、黑色、白色和灰色的文件夹塞得鼓鼓囊囊的,也挤在书中。房间左边角落的白色写字板旁边,甘地正从一张略微皱折不平的画像里凝视着他。在默赫许的脑子里,那件烦心事每隔几分钟就会跳出来,搅得他心绪不宁。
鲁米为什么要在练习本上写那样的话呢?这个疑问勾在他的良心上,像细细的牙科探针轻轻穿透柔软的牙龈那样,时不时地刺他一下。她为什么要那样写呢?我和莎伦·拉弗蒂、朱莉·哈里斯、莉尼·洛珀一起去树林玩。她们让我玩垒球,和跑柱棒球很像,但只有两个垒。莎伦说:“走吧,到我家去拿垒球和球拍。”我们到了她家之后,在门外站着,莎伦又说:“鲁米,我要先去问问你能不能进来,因为我妈妈不喜欢有色人种。”然后她就和其他人进去了,我在外面等。
谢天谢地,她出来告诉我我可以进去。我们进屋,吃了刨冰,拿了球拍。拉弗蒂太太在花园里晒日光浴,晒得浑身发红。我们拿着球拍,在树林里玩了垒球。
“有色”这个词在他脑中产生的联想是一张圆脸,脸上被褐色的蜡笔不均匀地涂了厚厚一层,就像早些时候鲁米不情愿画的那些傻乎乎的小人儿。
他再一次看向左边角落里的甘地像,画像里的甘地干瘪瘦小而神色坚决。如果放在他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又会怎样看待这件事呢?那时,他们终日与理念为伴,就像是舒舒服服躺在茧里的蚕。托洛茨基①派,甘地共产主义者——他们为自己找到许多称呼。他们嚼着槟榔,一边回味唇齿间的涩味,一边琢磨着阶级斗争和非暴力是否可以兼容。他们会怎么评价这个词呢?又会怎么评价他读过那段话后和鲁米进行的对话呢?“你喜欢学校吗,鲁米?”“我不喜欢那些霸道的人。”“什么霸道的人?”“那些对我不好的人。”“别让这些事情影响你。你已经十岁了。”“十岁又怎么样?”“你应该像丛林中的老虎。就像《森林王子》①里的虎王一样。”“什么意思呢,爸爸?”“意思是如果有人打了你,你要打回去。如果他们打你一下,你要打两下。”这些话从他嘴里脱口而出,诚实得就像出膛的子弹。然而他的眼睛开始跳,于是他把脸扭向一边。他想:也许你听到这些话很吃惊,好吧,其实我也一样。但你不会成为一个受害者。我绝不允许。
他选择居住在这个世界,并把他的后代摆在他世界的中心,看的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会怎么想呢——海德拉巴大学②的那群人——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呢?说到这里,他现在的朋友怀特福特——曾与他一起在加的夫③念博士,本人也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又会怎么看呢?又一列火车开过去,车身嘎嘎作响,像偏头痛发作时的脑袋。屋子也跟着微微颤抖,好像震得甘地像也跳了一下。窗玻璃上挂了一抹傍晚的微光,使甘地的半边脸变得模糊不清。有色?她为什么这样写?现在是下午四点,他打算提前结束今天的工作。他已经改了四份试卷,而此时房间里几乎没什么亮光了。默赫许把水笔的笔帽旋上,将笔放入棕色涤纶上装的外口袋里,好让哑光的不锈钢笔身露出来。这支笔是什琳送给他的礼物。生下鲁米之后,什琳就出去工作了,买笔的钱是她从头几个月的工资里省出来的。这支笔的年岁差不多和鲁米一样大。十年过去了,它摸上去依旧冰冷光滑,笔身上没有任何能看得出来的划痕或凹陷。即使是现在,当他想起这支笔的象征意义时,仍然能感受到这件奢侈品给他带来的那种夹杂着负疚感的快乐:笔是学识和智慧的工具,但又是浮夸的工具。他扣好外套,把试卷摞在一旁,放下百叶窗,然后锁好门。他胳膊下面还夹了两份硕士论文,打算带回家看。
五年前的某一天,鲁米回家后宣布戈尔德夫人要来家访。当时她五岁,上小学一年级。戈尔德夫人来访的那一天,默赫许和什琳提前做好安排,早早下班,三点半前都回到了家中。什琳开始炸巴吉①,而此时默赫许早已换好衬衫和领带,坐在客厅里陷入了沉思。当戈尔德夫人到的时候,鲁米正牵着她的手。
“从学校到家里这一路真是愉快啊,瓦西先生,瓦西太太。”她一边说,一边让鲁米先进屋。
鲁米突然安静下来,不自在地扭动着身体,抬头看爸爸。默赫许盯着那位老师用氯化氢漂染过的头发——那发型高低起伏,线条圆润,像是黄油糖浆搅拌后又摊开来制成的一道甜点。他困惑了。面对戈尔德夫人散发出的灿烂笑容,最自然的反应理应是松一口气,可他的内心却犹豫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