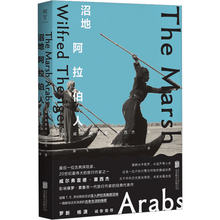毫无疑问,句子的肌肤总是在我的工作中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位置。即便我不在我的桌子前,它们生动的形貌仍在不断地萦绕着我。我重复着字词、节奏,我尝试着铿锵,我安排着回声和断裂。在我心中,这就像深深的水流那一再反复的、能够预见的、不断有所意外的运动,这深深的水流交缠、拍击、浸淹,一下子就把粉红色花岗岩的岩石连根暴露无遗,随之又轻柔地摩挲着这些水淋淋的、被吐着泡沫的涡流冲刷得光溜溜的岩石。
这一不知疲倦的活动——其耐心之手缓缓地贴合了言语既坚实又流动的材料本身,贴合了它的韵律、它的结构——明确无疑地体现出一种首先是感觉欲念的特点。但是,让我同时十分关心的字词的那确切而又暧昧的意义,也将随之展开一个新的场,一个调性、不谐调、遥远和谐、固执唤回的场,也就是说,整整一种音乐,人类嗓音在无以计数的音域上的音乐,尖利和低沉的欢乐的音乐,拍打着布列塔尼古老坚实土地的大海的音乐。布勒东、特里斯当·科比埃尔①、瓦雷里、奈瓦尔、洛特雷亚蒙,我一边行走,一边背诵,或者一边洗澡,一边背诵,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天花板,吟诵我那些老战友的歌谣:水晶般波浪的古老海洋,我向你致敬,古老的海洋,再一次向你致敬。
而现在,依然在大西洋的一处海岸上,那是蒙得维的亚北面长长的荒凉海滩,突然间拥满了金光闪耀的沐浴女子(在阳光下欢快地畅笑,顶着高涌的海浪,任它们拍打她们,掀翻她们,在白色的泡沫中变得支离破碎,到处渗入到她们身体中),随后重又空空荡荡,一片金黄色的细沙处女般地静静仰躺着,偶尔可见深深卧息着一枚肉红色女阴似的贝壳,脆柔的边缘缲着一圈珍珠色,或是一团搁浅的棕红色海藻,散乱着长长的毛发,还有一只窄小的舞鞋,后跟又尖又高,鞋面缀满了闪耀着金属蓝的闪光片,上面还缠挂着细细的珊瑚枝,或许是不久前某次海难的见证。
就在这片景色最隐秘的深层,亨利-德·科兰特当年或许经历了他尚有疑问的乌拉圭历险之行。狂暴而又单调的景色,这样数十里①又数十里地延伸着,一直延续到巴西的边境,在连绵逶迤突兀而出的花岗岩礁石中不断重现,任凭风吹浪打,威风凛凛的绿色浪潮滚滚奔涌,发出一记又一记震撼人心的拍击,打在平展展的滩涂上。每一记涌浪过后,闪着太阳光咝咝作响的白沫缓慢地舔舐着海滩,然后退回海洋,在身后留下一面转瞬即逝的活动镜子,一时间里,镜中倒映出一群群纹丝不动的海燕和海鸥。不远处,海岸上突兀一片岩礁,挡住了这里的地平线,三只又大又黑的鸬鹚栖息在岩礁的最顶端,仿佛在站岗放哨。
在这个地方,形状浑圆的岩石群之间本已很深的海水,似乎流动得不那么激烈,海浪只是在离海岸更近处,在那微微内曲成椭圆弯弓形的宽阔的沙土滨湾,才咆哮出声,而那多少有些峻峭的岬角,那长有强大忍耐力的植物、在古老土壤上杂七杂八地隆凸着水晶状堆积物的岬角,则向着远处的大海伸展而去,最后几处孤立的暗礁还使它在海中延伸出好几米。那里,水浪的涌动显得更加缓慢,不那么喧闹,几乎平平静静,在无精打采的摇篮曲般的曲调下,无疑也更加隐约。它贴着一面阴暗峭壁,有规律地上涌下降,随后,伴着一阵猛然的、无以预料的跃动,一下子就淹没了整块岩礁以及它所有的邻居,甚至还没过了鸬鹚宽大的脚爪。鸬鹚聚精会神,镇定自若,紧紧地附着在看不见的粗糙不平的石英晶体上,然后,涌浪转成白色的漩涡,穿透坑坑洼洼和断断裂裂,消退下去。
在他童年时代,人们常常给他讲这个故事。今天算来,它可以追溯到六十多年前。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在离布雷斯特不远一个叫做“猫咪”的地方,就在锚地的人口,一个如刀劈开悬崖的小港湾带斜坡的码头上,一阵沉闷的海浪就这样袭来,把他卷走。我那时能有几岁?也许三岁或者四岁吧。我们跟着妈妈,还有妈妈最小的妹妹玛尔塞拉,一起出门兜风,坐的是玛尔塞拉丈夫的黑色大汽车,他的名字叫安托南。正如这一容易使人联想到罗马时代的名字所显示的,我的小姨夫不是布列塔尼人,而是普罗旺斯人,他会游泳,这实在是幸运,它在这一天给了我好运。我们下了汽车后,便轻松悠闲地小步走在护岸的坡道上,花岗岩的斜坡不很滑,只有底部被清亮的海水轻轻地来回拍打着。正在这时,来自大海深层的一股莫名其妙的涌浪,突然猛一下子掀上斜坡,把我一卷而走。我的姨夫安托南赶紧一步,连衣服都没有脱就跳下了水,没费多大的劲,他很快便把我捞了回来,带回岸上。看起来,我还没有呼吸到致命的液体元素;我仅仅只是像人们说的那样,痛快地喝了一大杯。我们全部赶回汽车中,我被妈妈紧紧地抱在怀中,像是一包什么珍贵的东西。我们抄最近的路回到喀朗果夫,好把我们弄干,给我们取暖,讲述历险,由此结束我们的远足。
正是这一故事,后来随着我渐渐长大而成百次地复述,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事件本身过于匆促,或者过于久远,并没有给我留下一丁点有意识的回忆,尽管我常常重见那个曾经冒出过魔怪的、其名字具有预言性的凹洞……“猫咪”,猫崽,毛发丝光滑柔的纤弱的小猫,女人性器官的最令人安心的形象,猛然间张开了它那满口鲨鱼牙的猩红嘴巴,把我生生地活吞下去。
第二次,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当时我正在安的列斯群岛的法属岛屿,懒洋洋地观察患病虫害的香蕉树腐烂的根茎,它们已经被一种叫做(用拉丁文)国际脏虫的可怕象虫悄悄地咬死了。那是在法兰西堡的海湾,4月份的一个快乐的星期日,我又一次幸运地从海难中逃生。作为一个毫无经验的船员,我上了一艘十分小的帆船,与它的主人为伴,他是一个体操教练,热衷于水上竞速运动,刚刚马马虎虎地修造了他脆弱的小舟,配置了一杆与小巧的船身不成比例的大桅杆,帆布也装备过多。我的角色局限于“补偿平衡”,也就是说,当这巨硕的帆索架杆令人担忧地倾向一边时,我便要跑到它的对面去,仰身压躺在船沿上。
但是,我的同伴使我放宽了心,因为他在海风相当猛烈的情况下,从容自如地操纵着。我们手舞足蹈地漂向朗比小海湾方向。正当我们一路顺风地漂流时,一艘当地人的大型渔船切入我们的航线,整套红色的帆篷披挂在外。勇敢无畏的体操教练继续驾船径直驶去,内行地估计出,我们将绰绰有余地偏离开它木色阴暗的粗大船尾,却没有看到它拖带着的一条粗线挡住了我们的航道。在最后的一瞬间,他才发现情况不对,可能是为我们不太稳定的平衡考虑,或是不打算切断被拖拉的速度和它自身的重量绷得紧紧的捕鱼绳缆,他猛地改变了一下方向,顶风而行。几秒钟之后,我们就苦苦挣扎在沉船的周围。帆船已经完全倾覆,船体被它过于沉重的桅杆和浸饱了水的帆布拖向深底。只有一点点还露在水面上。我已经说过,作为诺曼底水手的忠实孙子,我却从来不会游泳,尤其是在大海的涌浪中,即便这海浪涌动的幅度太大。于是我狼狈地扑腾着,试图抓住什么不时漂浮在水浪凹处中的东西,当作救命稻草,依靠在上面。我的同伴对我喊,让我别靠在他身上,也不要靠在随便什么东西上,因为我会适得其反,拖住别的东西一起沉下去。他非但不过来救我,反而去拉缆绳,这是他注意的唯一物件,他一只手紧紧抓住它,同时用另一条胳膊和两只脚拼命划水。
我已经看到死神降临,觉得在这样一个朗朗晴日死去,真是一件蠢事,我还有那么多的作品要写呢。幸运的是,捕鱼的人远远地认出,艺术家遇到了危险,世界即将失去他,终于决定掉转船头,前来救援我们。经过两个来回,他好不容易把我扯上了甲板,我当即瘫倒在地,筋疲力尽,大口大口地吐着咸涩的海水。在人们并不需要使用的救生圈上,我读到了这条船的名字:“奥尔加”,它属于我们祖辈与海上魔怪传奇性搏斗中的可怖的黑色逆戟鲸。①
奇迹般逃生的约拿②,我的鲸鱼被捅开了肚子,在某几次确切的溜达中,把我吐出在最近的荒凉海岸上。经过差不多两小时的努力之后,肌肉发达的游泳好手来到了我身边,牵曳着他那珍贵的破船,他也折腾得筋疲力尽,但有更多的理由,不管怎么说,他很高兴看到我还活着。他说,他当时马上就想到,若是换一条船(即便不减缓速度的话),他是可以谨慎地安排好的。一般情况下,这里的鲨鱼不会游得离海岸那么近。就在我们的头上,草木葱茏的山崖上有一座小小的石头房子,门窗狭小,战争期间,安德烈·布勒东曾经被拘禁在此。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