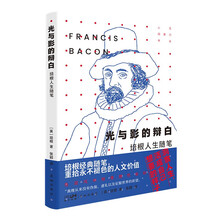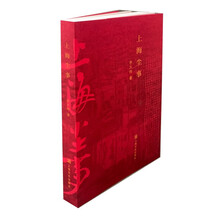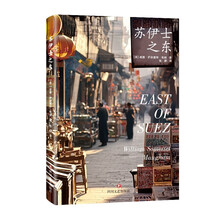土地承受一切,也记录一切。土地录进了江南六十年的变迁。一粒土壤,一个水分子,就是一个昨天,预示着一个明天。
要问我的家,我会说,不在姑苏城里,苏州城里的家,那是候鸟的迁徙地。我的家在江阴农村。出江阴东门十里,从长江边黄山炮台向南拉一条直线,相交处就是我的家。前几年,站在江阴长江大桥的南端引桥上,可以看到那黑的瓦白的墙。
那个村叫北湖埭,中间有个大水塘,塘西叫北湖西埭,塘东叫北湖东埭。北湖是什么意思,不清楚。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通信地址,叫江阴东门外蒲鞋桥北湖东埭,蒲鞋桥是个集镇;后来叫江阴县要塞公社新华大队;再后来叫江阴市要塞镇新华村。向南-二十里,翻过一座山,就是大名鼎鼎的华西村。
实际中的村,有几种概念,最大的是行政村,新华村就是行政村,由四五个自然村组成;其次是自然村,一个一个村落,有大有小,北湖东埭就是自然村;最小的是生产队,后来叫村民小组,农民口中的“我们村上”,这个村实际上是生产队。生产队是农民活动的天地,几十年内是经济核算单位,是农村最基本的细胞,同样是一个政经合一的组织。我跟着村民,我所说的“我们村”,也是说的生产队。一个村的半个世纪,实际是一个生产队的半个世纪。
江阴的村子密集,都很大,一字长条里把长,有—二百户人家。村与村之间,仅相距一二里。村前村后是农田、水塘、渠道。我们那个村中间有一条小河通进长江,也有潮起潮落,河水是浑的,塘水是清的。河岸塘边有几棵青丝飘飘的杨柳树。
我们那个村几乎都姓徐。徐家的祖宗徐僖公是明朝兵部尚书,有家谱记载,我在《中国名人大辞典》里找到了徐僖公,江阴城东南岐山脚下有他很大的墓,还有石人石马和高大的祠堂。村上留有楼房遗址和养马的厩房。20世纪50年代,我看到一箱的家谱,可惜“文革”中被我母亲烧掉了。徐僖公的墓,文管部门作了保护性挖掘,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江阴人多田少,全县人均在一亩半左右。我们那村,就是生产队,三十来户人家,一百来个人口,有水田一百三四十亩。每户占的地相差不很大,多则十来亩,少则一二亩,无田的佃农几乎没有。为何如此平均,可能与人多地少有关,都是活命田,出卖的人家极少,有钱有势的人家也几乎没有,形成了土地兼并的真空状态。我家祖上的田,经几次分割,到我父亲名下已只有水田二亩半、旱田三分,到新中国成立时人均不足一亩地。
我家和别人家共有的水地叫十亩地,我家的田在中间,长长的一条,耕种很不方便。父亲早逝,留下的印象,只有水桶上农具上“徐宝余记”几个挺工整的字儿,还有阁楼上的几捆发黄了的书。我和我母亲、哥哥,就守着这三亩地度日。田靠我哥哥种,农忙时在山观的舅家来帮种,我六七岁时也下地了。一年两次收成,一稻一麦,丰年可以吃饱,灾年就要去买山芋充饥。一个挥不去的印记,山芋吃怕了,肚里老胀气。羡慕村上田多人家,麦收后还吃白米饭,而我家三餐麦粉粥,隔天中午吃顿麦片饭。麦粉要手推磨出来,我五六岁就推磨,锡剧《双推磨》多好听,推呀拉呀转儿的,推磨难挨呀,人和磨盘差不多高,拉过来推过去,小脑子里经常想,什么时候不推磨。
我们村那一百多亩地,地形地貌,新中国成立之后几十年间并无多大变化。要说有变化在50年代中期,原来有一个大的土堆,有半亩地大,说是太平天国时“长毛”(太平军)被清兵杀了堆葬而成的,是不是曾国藩的功劳不清楚;还有一个十来亩的小岗丘,上面有茔地,有旱地。我们那里几乎家家织布,棉花要到苏北去买,我母亲年轻时也去买,早出晚归,有时来回要两天。傍晚,我和我哥哥就立在岗丘最高处,等我母亲挑着棉花从北边路上出现。太平军的墓和小岗丘,平整土地时平掉了,成了平镜似的水稻田。
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就是农村生产关系。六十年间,与江南农村每个村子一样,我们村的地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这就是: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家庭联产承包。一次二次,我在农村都经历了;第三次,也看到了。三次变迁,地没有多大变化,却是农民命运六十年历史的关节点,几乎是一个甲子的“三农”的全部,什么叫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三次变迁就是调整的全部。我所经历的、看到的、所认识到的,与听到的、文件中看到的,有同有不同。
六十年后,怎样看江南农村的那次土改?在我看来,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新中国成立时,江南土地兼并状况如何,不大清楚。从我们村和周围的村来看,土地兼并并不严重,户与户之间大体平均。一个行政村三四百户,仅一个地主一个富农,其余全是中农和贫下中农,中农的比例也不高。地主家有地四十亩,富农家有地三十亩,这个地主这个富农都种地,雇佣的长工都是季节工,并无《半夜鸡叫》里“周扒皮”那样的劣迹,严格来讲,他们不是地主不是富农,开斗争会农民恨不大起来。不过,农民还是热烈欢迎土改,分地时可以称之为兴高采烈。这是我在六十年中,仅看到的一次农村集体大欢乐。那时土地金贵呀,土地就是生命。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