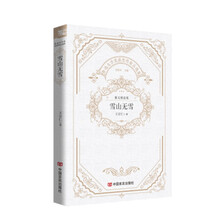《别处》:
每次在五金店门口被婆婆叫住,没有一个小时是走不掉的,有顾客来买钉子、水嘴什么的,她就小跑着应付,嘱咐我:等等啊,等等。她家除了五金店似乎还有生意。她是老知青,返城后在国营五金店上班,挨到国营两字消失她就成了老板。二三十年她整天和这些奇形怪状的铁疙瘩打交道,当年用漂亮的眼睛瞅它们,现在戴上老花镜瞅它们。假若让我吃三十年韭菜,天天吃,吃成富翁,那我也不干。
四楼基本上就我一个人,二楼三楼也不是总有人,这是那年的九月到十月中间,旅游旺季还没到,旅馆相当萧条。一楼是他们的起居室、库房、锅炉间,就旅馆本身来说它给人一种小麻雀的齐全感,缺失的不是这个。整天坐在接待柜台后面的媳妇大约三十多岁,她和她未出世的孩子将柜台撑满了,她不说话更不爱笑,起码我没看她笑过。她埋头打毛活儿的样子像是凝固的,起伏波动的针和线带着太阳的光芒如同刺着一个雕塑。她目光一旦离开手上活计立刻变得暗淡无光而又闪躲。开始我不明白她身上为什么没有一般孕妇身上洋溢着的那种成熟谷穗的安静和宁谧,她像是被手上的毛线缠住了,毛线正把她拽往远离她呼吸着的空气和所在的时间。她丈夫个子不高,透着精干和聪明,这是个吃饭也不大摘墨镜的人,不知是有意让白己与别人拉开距离呢还是不肯让人清楚地看到自己,都一样。如果拎个相机,他更像海滩或公园拉游客拍照的人,可他手上拎的却是锤子、锯条之类,从一楼到四楼不停地做事,不说话,不停止。我每天到隔壁快餐店吃饭,下楼时公公、婆婆、媳妇围桌细嚼,另一个座位上的垫已经皱了,空碗上横着用过的筷子。一天晚上很晚了,他还在四楼钉什么,因为要看一场球赛我就婉言催他收锤。这几天走廊上堆满了新购进的床、茶几、衣架,很少有人用沉默来迎接这么蒸蒸日上的生意。“又进这么多家具?”我问。他停下活儿,二拇指捅捅墨镜,啊了一声,露出镜外的嘴角和面积不算大的两腮显出苍白和艰忍的线条。他转身要下楼,又像忘了什么似地回头说:“想把四楼房间搞得好一点。”也许是不怎么听到他说话的缘故吧,他一开口就像送礼,音调里有一种令人感动的东西,如同一件阁楼上轻易不动的老乐器,被一缕光线拨响了。之后不久我就听说了他家的事,不是听听拉倒的事不关己而是心里七上八下的。我觉得,他们一家的经历——说了的,没说的,堆在走廊一端;而我,住在走廊另一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死了。男孩的聪明和顽皮都像日本的一休,旅馆里充满了他的童声,谁听了都会站住,谁见了都想抱抱。让人无法相信,他还没有来得及上学前班就死了,乌云降到这家人头上,之后全家人都用默默干活来忘记不幸,每人手里抓紧一件工具用以支撑,公公抓住的是一只旧算盘,婆婆抓住的是五金店任何一件器物(回到旅馆则抓紧剪鸡头米的剪子),丈夫拎着锤子或锯,媳妇手中是永远理不清的毛线。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