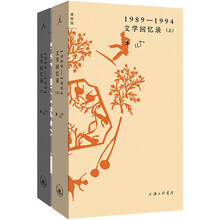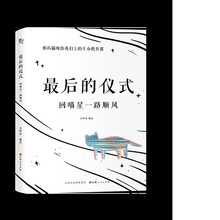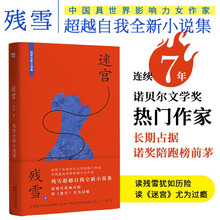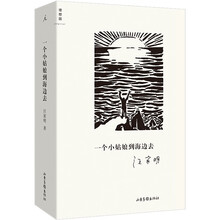怀念周绍良先生2005年6月中旬,我应邀赴伦敦,继续从事英国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编目。8月23日伦敦时间上午9点,接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李际宁先生电子邮件:“8月21日晚21点30分,周绍良先生去世。近三天,在他的家里(就是靠通县的乡下)设灵堂吊唁。”
当时真是愣了。在给李际宁的回信中,我说:“走前已经听说周先生住院,但事情实在太多,你是知道的,国图图录的事情、冯先生的事情、《中华藏》样书的事情,加上一堆论文审读及答辩,算着小时计划工作。连芳芳(我女儿)从日本回来,我也未能与她好好说一会话。所以未能去医院探望,总希望他能早占勿药。没想到这就走了。我受周先生教益、帮助良多。住院时既未能去探望,此刻又不能亲去吊唁,实在于心不安。”
我首先想到的是可以通过白化文先生转达我的哀思。可没有白先生的电邮信箱,于是立即给他的弟子杨宝玉女士发去电邮:“惊悉绍良先生21日因病故世,不胜悲悼。我受绍良先生教益、帮助良多,一直无以为报。前此按照先生的企划,计划把我的敦煌已入藏佛教文献目录编入先生主编的佛典目录中,没想到工作正在进行,先生竟然西去。我现在没有先生双桥的地址,也没有白化文先生的电邮信箱。麻烦您把我上面的意思转告白化文先生。白先生去吊唁,还请在绍良先生灵前代为致意。”
想到敦煌已入藏佛教文献的目录,就想到为周先生主编的中国古籍目录释家类奔忙多年的李家振先生。便马上给李先生发去电邮:“惊悉绍良先生不幸故世,深为悲痛。先生前去吊唁,望灵前代为致意。我受绍良先生帮助、教益良多,无以为报。原以为这次的目录可以代绍良先生了却一件心事,却又留下遗憾。”
第二天上班,接到李际宁23日晚上发来的电邮:“23日下午(北京时间14点),有庆(国图善本部善本组组长程有庆——方注)往周绍良先生家吊唁。……有庆回来告我:白化文先生为您在英国表示哀悼向周家人作了说明,程毅中先生代笔签名。”
无论如何,未能到周先生灵前鞠躬致哀,心中多时歉仄不安。因为我受周先生的恩德太多。在上面几份电邮中,我都提到受绍良先生帮助、教益。这绝不是应景的客气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在《敦煌佛教经录辑校》前言中这样写:
本书得以顺利编纂,首先要感谢周绍良先生。这不仅因为周先生代表编委会具体负责本书,还在于周先生对本书的编纂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从选目、洗相到录文体例、格式、题解的要求等,不嫌其烦地指点。尤其是本书原计划抄写后照相排版,周先生专门为我安排了抄写人员,用规规矩矩的正楷把全书抄写一过。由于格式与抄写纸张的变动,不少文献还抄了两遍。其间转稿、审稿不知花费多少精力。回想我多次到广济寺找周先生,他顶着炎炎烈日为我取稿的情景,私心区区,实不能已。
在博士论文《八一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的跋中,我这样写:论文的写作,除了任先生(任继愈先生——方注)自始至终的指导之外,黄心川、季羡林两位先生在指导我确定选题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周绍良先生对我的帮助与指导也是我终生难忘的。大到论文的结构篇章,小到一些具体的论述,周先生都不厌其烦地一一指点。不仅如此,周先生还主动提供家藏叔迦先生亲笔批点的书籍、所抄录的敦煌卷子及传世文物供我使用。他那儿的书籍资料,只要我能用得着,随时可让我拿走。扶掖后进的苦心,为人之高尚风范,实在叫人感荷不尽。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老一辈的悉心培养,绝不会有我们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凝结着老一辈学者的心血。先生们的恩情,我是无法回报的。我只有更加努力地搞好自己的研究,以更好的学术成果回报先生们;只有以先生们对待后进的态度为榜样来对待比我年轻的朋友们,为他们的成才尽我的全部力量,以此报答先生们的栽培之恩。
所以,我与周先生虽然没有师生的名分,但心中从来把他奉为人生道路上一位重要的老师。我认识周先生是1984年跟随任继愈先生攻读佛教文献学开始的,至今已经超过20年。周先生是著名的佛教文献目录学专家,对佛教文献目录之熟,国内少有。所以任先生给周先生打招呼,让周先生多指导我,并让我遇事多请教周先生。那时周先生在法源寺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工作,我每月一般要去一、两次,有时甚至更多。至今记得顺着丁香簇拥的甬道,到后院佛教图文馆找周先生的情景。每次带着问题去,带着周先生的指教回来,然后再看书。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周先生之所谓也。后来周先生主持佛教协会工作,驻广济寺;我便开始向广济寺跑。1986年有半年左右,任先生让我理顺《中华大藏经》的工作流程,这段时间,为了《中华大藏经》的工作,包括向有关佛教寺院商借校本等等,跑得更多。至于编纂《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与后来撰写博士论文时周先生的帮助、指教,上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