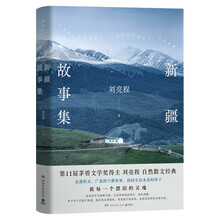在天津很难使人注意节季的变迁,顶多不过棉衣易夹衣,夹衣又易单衫而已;而在北平却不然,北平的胡同是十足的表现着春夏秋冬的不同,一到春天,胡同里最易起小旋风,薄薄的一片土卷着柳絮,非常的富有诗意。下起小雨来,胡同内就不易走人,没有事最好不出门,打几个子儿的烧酒,买一包落花生一吃,坐在家里听门口卖青菜萝卜的吆喝,是另有一种风趣的。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就有卖青杏的,卖樱桃桑葚的,还有卖各种花的,尤其是落过雨之后,花儿更显着鲜艳,再加上卖花的富有艺术味的嗓子,颤颤的一声:“买架竹桃来,石榴花来!”真令人想起放翁的名句:“小楼昨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一到夏天,人们热得四体流汗的时候,正午却有小孩子卖冰核(音胡)的,挑着两块冰,一边喊:“冰核来,冰核来!”一边却飞也似的跑出胡同那头去了,因为卖冰非跑不可,如果像卖花的那样文绉绉的,卖不了几个主顾,冰也就融化完了。这也是一种趣味化的买卖,因为卖冰既赚不了多少钱,而在夏天正午的时候,还要担着冰快跑,在我们看来当然是很受罪的,然而小孩子们却以为跑跑玩玩是够趣味的。
秋天一来,更易落雨,落过几场雨之后,树上的叶子几乎就像随着雨也落完了,憔悴的黄叶零乱的在胡同内滚来滚去,假若有诗人要想“独寻黄叶路”的话,不必到什么郊野的地方去,在北平的胡同内就可以有这种风趣了。黄叶飒飒的一声,跟着卖玉米花,凉炒豆的就来了,还有卖新落花生的,这几种卖东西的声音,无异就是告诉人“预备棉袍子吧”。果然秋天没有多少时候就过去了。我记得仿佛是鲁迅先生说过,北平没有春秋,颇有点道理,假若冬天一延长,夏天一提早,把这春天却无形之中越过去了;冬天提早,夏天延长,秋天也就很短了。虽然是这样,然而北平的卖东西的,对于季候,是一点也错不了的。
北平的冬天更能令人领略出一种特殊的况味。现在差不多的人家大概都装上洋炉子了,在从前却没有,都是小白炉子,如果在彤云欲雪的黄昏,屋中不必点灯,小白炉子内的煤球红红的,可以照见人的须眉,屋内充满了淡红色的光,薄薄的窗纸“席席飒飒”的一响,跟着就是风门子被风吹开,“啷”的一声,又关上了。这种特殊的风趣在当时多不注意,而我们几个朋友却正在围着炉子烤手,有的手里抱着茶壶:作诗,大概谁也没有那种闲散的心情,下一盘围棋,倒可以使人忘了冷,再不然早早的钻进大棉被里去,躺着看书,躺着吸纸烟,这时不晓得外面是否落了雪,也更不注意外面的风,然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却被风吹来一声“萝-卜来-赛梨”的尖厉的调儿,有时还会同火车的哨子成一个合奏调。这时我们躺在被窝里的心情,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怅惘吧,谈不到;悲哀吧,更不是;喜悦吧,绝没有一点,只是心里空空的,觉得有点迷惘,大概这种情绪是在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七情之外的,所以没有法子可以形容当时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再其次的就是我领略出北平胡同的不规则的美,比如一个大红门楼旁边,就许有一个小黑门,小黑门里就许有两棵大枣树,而胡同又都是弯弯曲曲的,比如说狗尾巴胡同,真的弯的像一条狗尾巴,铁狮子胡同,虽然没有铁狮子,然而却有一对石狮子。北平胡同的名字,大概都是名副其实的,而天津却不然,无论大小的里,不以德名,就以义名,比如说崇德里,而这里面的人,未必就真崇德。房子都是一样的形式,排得密密的像鸽子笼,令人见了,便有一种不快之感。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