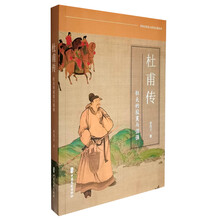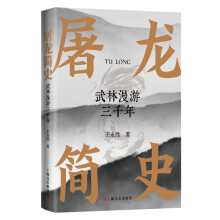第一章<br> 阴霾的天穹下,一丝风也没有。森森的雾从潮湿的大地升起,泛着死白的颜色。雾气纠合聚集,缠绕盘旋,在苍茫的地上投下影影绰绰的痕迹,越来越浓,逐渐翻过山冈,向下沉沦,朝着岗下那无数具腐败的躯体飘散过去。<br> 这些躯体各自以扭曲的姿势呈现在天地面前,或蹲或跪,或伏在残破的马车上,或插在粗大的木藜上,还有的相互扶持屹立不动,尽管彼此的刀剑都穿透了对方的身体。更多的则陷在地里,合着血泥,再辨不分明。<br> 仍有几处焦黑的马尸在冒烟,不过火几乎已经要熄灭,使得烟看起来像白色的阴魂,晃晃悠悠,有气无力地往上瞎蹿。放眼望去,广漠的大地上,只有食腐肉的乌鸦还在尽力撕扯扑腾,其余一切都已归于死寂。<br> 若不是那双眼睛问或的一轮,谁也不知道在这烧焦的马车下,在这重重叠叠的尸体旁,竟还有一个活着的--或者说,还未完全死透的人。<br> 这双眼睛躲藏在一簇散乱的头发后面,僵直地瞪向前方;头发往上,是一系脏得失去本色的破烂的麻布。麻布从头到脚紧紧裹着瘦小而佝偻的身体,无力地抗拒着阴雨寒雾。<br> 这人吃力地蹲着,两只纤细脚上没有鞋袜,挤在水汪泥泞里一起瑟瑟发抖。大地肆无忌惮地通过这双脚上夺取生命的一切,脚也因此异常的惨白,连最细小的血管也透过皮肤,显出可怕的青色。<br> 不知道他究竟在这里游荡多少天了,双脚沾满血泥,早已冻得没有一丝感觉。接近中午吋分,当翻起最后一具尸体时,他心中不知是失望还是宽慰--父亲……并不在这死去的四千…百三十五人里。<br> 不在这里,但并不意味着父亲没死。也许更糟,死在僻静无人的地方,连个收埋之人都没有。<br> 但或者……或者还活着罢。仍披着厚重的盔甲,提着带血的枪,等待下一次的搏命厮杀。<br> 他这么想着,再一次失去了方向,站在…片腐尸残肢中,心中无比困惑,只觉得支撑着自己这么多日子以来的希望终于熬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那时节,马车上的火还没完全灭,那些零星的火苗似乎仍有点温暖,于是就势蹲下,看着火,什么念头也没有。<br> 后来天阴下来了,地也冻起来了,雾也升起来了,他仍不知往哪里去,继续呆呆地看着。再后来,“哗啦”一声,烧焦的车架和一些分不清是人哪一部分躯体的东西倒塌下来,浸入血泥中。 火就这样熄灭了。 这声音吓了迷离中的他一跳,不过只有他的小心脏扑通扑通地乱跳了一阵,身体却一动不动--严寒己渗入骨髓,再难动一丝一毫了。<br> 他这个时候头脑出奇的灵光,想起了父亲曾说过的一个故事。说是大冬天,有人在雪地里站着不动,后来冻僵了想走也走不了,就那样僵死了。等到春天,人们见到他时,还站着呢。<br> 他于是想:我这样蹲着会不会死呢?若是死了,是否也是这般蹲着,到了春天,小草野花会不会爬满我的身子,就像花冠一样呢?他就继续保持着奇怪的姿势蹲着,一面想开在身上的到底是野菊好些还是紫浆花好些。<br> 他以为这世上只剩自己一个人了,却不知就在他冻僵的那会儿,有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出现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