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一张离台灯光源较远的,打着黄铜泡钉的皮质三人沙发上坐下来,靠沙发边摆放的是一张柚木茶几,之上,半杯早已冰冷了的浓茶被她随手取来喝了一口。
一股清醒灌人胸中,她怔怔的两眼望着对面的那幅被石灰水刷白了的墙壁:一幅上海市街道的详细挂图以及一盘日历恰好撕到今天这一日:1968年11月7日。之上一条鲜红的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五十一年之前的彼得堡,天气可要比现在冷得多了,但就在这滴水成冰的城市和季节里,在那一晚,阿芙乐尔巡洋舰向着冬宫的一声炮响,便有了苏联,有了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有了老贺十四岁参加革命,有了她十七岁的“马背女英雄”的称号,有了草鞋和灰布军装跨进大上海,有了他俩第一次在南京路的一家照相馆拍摄的双人照,她剪着短发,他戴了顶别着五角星的圆顶军帽,他俩都穿着一套带有部队番号的戎装,于是——便有了沪生。
“沪生,你又去哪里啊?——”她记得她大声唤叫他的时间是在今年的盛夏。她俯瞰在二楼阳台的栏杆上,几乎上半个身子都倾斜了出去。楼下花园里的树冠丛中一片热闹的蝉声,年近四十的她仍是相当有风韵,假如平日里不被她的那套宽大的蓝卡其工作上装完全覆盖了体态曲线的话。该凹的地方凹,该凸的地方凸,一件紧身的T恤衫将她身段的实情透露了出来。而她中年的不施任何粉脂的脸蛋上仍有一种肤质光滑柔嫩的诱惑。
她见到几条白衬衫的猴瘦身影从她家后门的树丛间一闪,便消失了。不知怎的,她最近一直在为沪生,应该说是为沪生结交的那伙人,担心。
上海东区这一带的英、法、日式洋房在他们进城之时,十有六七已人去楼空,即使没走的也被陆续迫迁了。军管会的封条一贴,之后便是他们那些人的搬进入住。司令家住楼上,政委家住楼下,在那时是很普通的事。孩子们从小便都玩在了一块儿。有一次,哭了鼻子的沪生突然来到厨房里拉住了她的衣角:“爸爸的官为什么当得那么小——不像海魂他爸?”
她愕然,“……官大官小不一样是为人民服务,你们的老师难道没这样说过吗?”
但他哭,哭得很冤屈。他说,他受不了他们老那样来嘲笑他,他赢了棋,对方就一定赖账,还伸出一个小指头来,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说,你算了吧,一个小处长的儿子,就甭来瞎充老大了,行不?
她将沪生的头——就是那颗现刻已被子弹洞穿了的——头,拥人胸前,轻轻地抚摸了又抚摸。那是童年时代的他,伏在她胸前,身高还不到她的肋腋处。她感到一阵难过,歉疚和一种小小的愤怒。
他最瞧不惯住在她家对面花园的那个海军司令的儿子了,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到了青春发育期更是长了一脸带脓头的粉刺,遇到漂亮一点的女孩子打对面走来,就会发出“(口欧)!——(口欧)!——”的挑逗声,吓得人家赶紧钻弄择道地避开。一直到他的老子那年因“反林(彪)事件”被隔离,之后又从隔离室中逃跑出来投了井,他的气焰才收敛了些。
与这种人打交道,沪生自然不是对手。他从本质上就有一种老贺的耿直和侠骨,这点知子也莫若母了。
其实,她嫁给老贺也就是在那么一刻钟的时间内,一句互道心思的对白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决没有丁点儿像现代男女间的那种连续剧的剧情。只是他们俩都觉得,而且组织上也认为,大家都到了该成个家,有个革命后代的年龄了,否则老一代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又靠谁来接班?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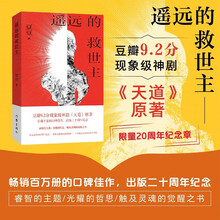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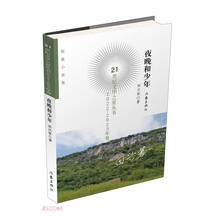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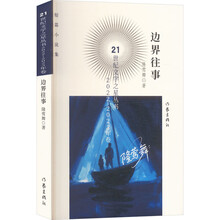


——贺绍俊(评论家)
吴正的小说是有记忆的小说。它的记忆着重在个人和时代的关系。他描写了人类心灵留下的巨大裂痕,以及这个裂痕如何弥合。
——李建军(评论家)
在当代文学中,吴正确实是一种十分个性化的存在。他的小说对中国文化的感悟,对历史的认识,蕴含着纯正的品格,真切而予人以启示。
——梁鸿鹰(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