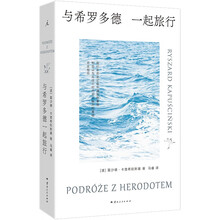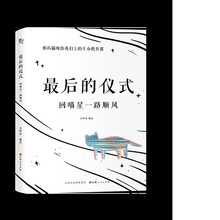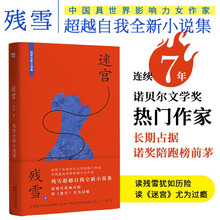扇
天气热起来,男的女的手里,出门时都摇着扇子了。将穿旧了的一件夹衫换去之后,我也想起:这时令是可以带扇子出门了。记得去年曾用过的那柄有朋友叶君写着秦少游《望海潮》词的福州漆骨折扇还并不破旧,中秋以后,将它随便放进了那只堆存旧扇秃笔的橱抽屉里,不知如今还可以用用否。现在是百物昂贵的时候,一副起码的粗粗地制成的扇骨,配上一页白扇面,也得要半块钱呢。如果去年的旧物,还拿得出去用用的话,何必再去买新的呢?
开了那只久闭了的橱抽屉,把尘封了的什物翻检了半晌,一个小纸包里的是记不起哪个年代收下来的凤仙花籽,一个纸匣里的是用旧了的笔尖,还有一枚人家写给父亲的旧信封里却藏着许多大清邮票,此外还有几副残破的扇骨,一个陈曼生的细砚,倒是精致的文房具。再底下,唉,这个东西还在吗?一时间真不禁有些悠远的惆怅。
那是安眠在抽屉底上的,棉纸封袋里的一柄茜色轻纱的团扇。
现在,都会里的女士是随处都有电扇的凉风可以吹拂她们的玉体,而白昼没有电气的内地城市里的女士是流行着鹅毛扇子了。团扇,当然是过了时,市面上早已没有这一注货色了,年轻的后生,恐怕只好在旧时代的画本中去端详一个美人的挥着团扇的姿态了。
我之看见了旧藏的团扇而惆怅,倒并不是因为它的过时,一种扇子的过时,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之所以觉得惆怅,只是为了这一柄团扇与我有些瓜葛。
那还是住在苏州的少年时候的事哩。
父亲因为要到师范学堂做事而全家迁苏的那一年,我才只九岁。到苏州之后的第一个月,我记得很清楚,我整天地藏躲在醋库巷里的租住屋里,不敢出外,因为我不会说苏州话,人家说话,我也不懂得。
但有一天是非出去不可了,而且是出去和许多的说苏州话的小朋友接触,那是父亲送我进附属小学继续读书的第一天。先一夜,父亲说:“阿宁,明天又要读书去了。”
我说:“哪里去读书?”
父亲说:“附属小学。就在师范学堂对面,放了夜学你还好来看我呢。我书经去和学咬里的先生说好了,仍旧是三年级……”他又回过头去对母亲说:“将来阿宁可以住到我学堂里去,省得每天来来去去地走。”
母亲笑笑,没有加以可否。我心里也木然,因为住在家里和母亲一处和住在学堂里和父亲一处,在我是都愿意的。
语言的难题又来到我心里,我痴想着:一群男女小同学在种着花的学校园里环绕着我,笑着我的家乡话。
过了一会,母亲笑着说:“阿宁,为什么发呆,为了明朝要进学堂去,所以不高兴么?”
我一声也不响,呆想着。年老的唐妈在旁边,又唱起她惯用的嘲笑我的歌词:“赖学精,称称三百斤。”
我被激怒着说:“谁想赖学呀,为的是怕说起话来给人家笑呀!况且,况且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走进陌生的学堂里去,叫我怎么好呢?”
父亲就说:“有什么好笑,就是人家笑,也随他们好了,过了三个月你一定也会得说苏州话。如果说没有人认得,那么明朝可以和对面金家的惜官、珍宫同去。明朝早上我带你去认识认识,搭个小朋友,以后也好一同作伴儿早出晚归,便当些。”
这样,于是在进学堂的那天早晨,我认识了生平第一个女朋友:金树珍,惜官的名字是树玉,是她的小两岁的弟弟。
在能说苏州话之前,很旮陸地,对着她,我居然很不羞赧地说着家乡的土话,而且说得很多,很琐屑。我告诉她城隍山的风景怎样好,西湖怎样好--其实那个时候的西湖,还是很荒寒的,而我也只跟了父亲,从清波门出去约略地玩了一玩而已。我在家乡的小学堂里读的是哪几本书。父亲有怎样几本好看的带图画的书,她不能全懂地听着我的奇怪的乡音,不时地微笑着。但我并不觉得如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的时候所想象着那样的脸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