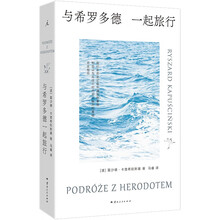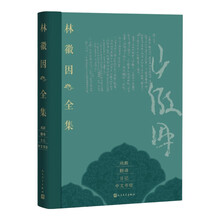遥远的风砂
在三月梢,已是幸福的春之尾了。而在卓索图盟,春风还藏在从西伯利亚吹来的狂飙的后面。
这里没有樱桃园湿润的香气。也没有“溜鸟”的嘹亮迷人的调子。有的是蒙古包放马声——长鞭连落的脆响,回音由山谷中传来。游龙似的马的突唇声“咴,唬——噢唔噢唔——”远道来的人,也许不承认这是马声,以为是荒原里一种奇异的野兽。马怎会叫出“噢唔噢唔”的声音来呢?——实际上这就是出名的“马啸”。当它突突的抖战着反抗鞭打的时候,在月夜,清风里,用前蹄趴着槽前的泥土,想起从前的恋人的时候。
说马啸是塞外唯一的声音,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原野里的鹰,是有着鹫一般的高傲的,不会学着雀鹰子,灰鹰,青鹰,……那样小家子气,一捕获了食物,就唧唧喳喳的叫的。它永远是悠闲的在蓝天里浮着,像一个神秘的巫婆,默念着咒语在兜圈子,像一片寂寞的云片。
黄羊子在塞外是精巧的造物。娇小的腿,如同袅袅欲折的竹节。竖起薄薄的小圆耳朵,常向远方去听。伊是神经质的,而且受不到保护,有一点儿风声草动,就只好拿起腿来便跑。伊的速率是可惊的,转瞬之间,依然是砂碛,远山,古道,成群的黄羊子早已不见了。……远远的天,飘来寥落的风响……
这就是我们这一行人长征中的伴侣。
还有羽毛和土色一样的不十分美丽的“百灵”,和它同属的头顶上鼓起一座英雄顶的“鹅儿翎”,在大地上凄凄的叫着。不要幻想它们能唱出在鸟市上金丝笼的家族那样婉好的歌声。不会的,在这愁苦饥饿的荒原上,它们不会的。它们吱吱啾啾的,看见马队过来,也不怎样想飞,好像长久没有遇见生人似的。
这就是我们在大塞中,唯一向我们招呼的亲人。
我们是昨天一早带着月亮出发的,昨无在郑家窑子吃了一顿“莜麦”面,我特意多吃了一点,现在肚里隐隐的还有点儿绞痛。今天一天没“打尖”,现在天色要晚了,在头顶上盘桓的鹰也忽扇忽扇的回家了。我们还在鞭着马跑,不知今夜宿在何处!
突然有人宣布:
“路走错了!”
全身都有点颓唐,忍冷,挨饥,风,砂,涉水,爬山……所为何来,为的是走错路?
马“肚带”又松了,下了马紧了一紧,实在不能再紧了。否则不但在感情上对不起我的拳毛芦花,而且在养马的经验上讲,要再紧着也就该“残”了。不过狠狠心,又紧进了一寸,我轻轻的拍着它的脖颈,我的马,从我用了不十分名誉的手段把它得到手之后,我们的命运便汇合在一起。它向天悲愤的长啸了一下,用前蹄趴着砂石,砂子在我的鞋子上打滚。
双尾蝎翻身跃下马来,默默的勘察地面,想寻出赶前车的脚印。那里有什么脚印!连牧羊的粪都没有,要发现了牧羊的粪,也是令人快慰的事情,总会断定离开人家不太远,至少也有羊圈子好走进。
他看了看前边的山峡。
首先发现走错路的贾宜就说:
“前边是山涧,我们走的是流水沟!”
这真叫人懊丧,双尾蝎领的路。“我看他‘猪皮胶’的脸色,就献不出‘番王宝’来,果然不差,他也认清鸟路!”煤黑子脸上每个红疱都挣得鲜红,沙声对我说,并不怕双尾蝎听见。
双尾蝎没有听见——一定是没有听见!很安闲的在流水沟上捡起了一块石头,用手拂去上边陈旧的马粪,把那块鹅卵石上上下下翻了一会儿,上边的一半都已剥蚀的有点粗糙,近于风化,底下的部分还非常光润。他扔了石头,又在石缝里,掘了半天。
“他想掘出臭蛤蜊来!”
陈奎告诉我:“要有臭蛤蜊就一定是流水沟?疑了。”
他掘了半天,空无所得,只捡出一片白贝壳,用黑色的瘦手指一捻就碎成石粉末了。他跨上马,把屁股欠起,望望前边的山头。前边没有层峦,非常晴朗,他用鼻子嗅了一嗅,空气很干燥,充满砂土气。
“走!前边就是龙门锁!”他决定的说。
走错路了!龙门锁!那有这便宜事,这一个南北极的差别,使人不相信了。
“妈的,你就惦着‘跳龙门’(‘跳龙门’是性交的隐语)了,龙门锁,龙门锁在山峡?,你走过这段路没有!”煤黑子发音中的山东大蒜味,愈加把他的激恨形容得义愤十足。我们都很同意他。陈奎向我看了一眼,眼光里充满了没有把握和疑问。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