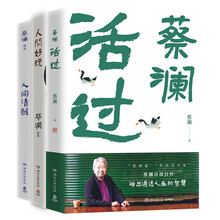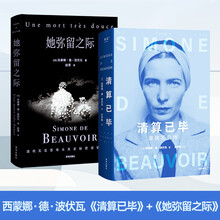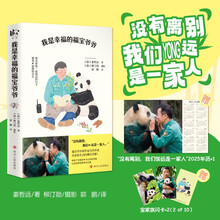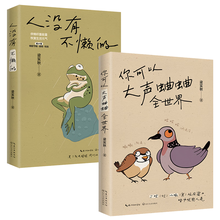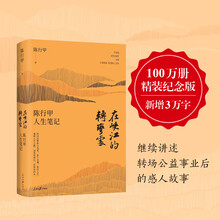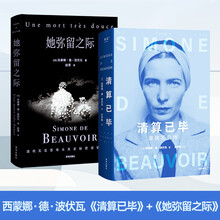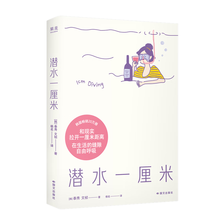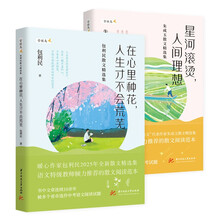岁月,不能回流
糖人儿,是最能逗人情思的了。
捏糖人儿的,是一位老翁。“老翁”,家乡人人都这样称呼他,就连怀里抱着孙子的老人,也这样说:“我们小的时候,就吃着他的糖人儿,那时,他就是一个老头儿了。”然而对于他,人们却又不详姓字,亦不知“贵庚”,那皓首苍髯,恍若隔世之人了。每年初冬,他悠悠而来,春天,又匆匆而去。来时,人们带着笑容迎接他;去时,人们又无限惆怅、依恋:糖人儿遇热而化,他会不会也“化”了呢?但到了下一个冬天,他又悠悠而来了。
一副担子,前是糖锅,后是坐凳。糖锅旁放着各种工具,工具有刀、剪、镊、模;坐凳上挂一布兜,布兜里面装着麦秆儿。锅里有半锅糖,黑红色,表冷而里热;老翁皮肤粗糙,动作迟钝,然而心灵手巧,外俗而内秀。择一向阳地方,打扫干净,这才操起那带着沙音的破铜锣,“咣、咣、咣”几下,便招来了全村的孩子们,一些性急的娃娃,还会牵着奶奶和妈妈的衣襟跑哩。
老翁从不讨价还价,能满足每个孩子的心:破盆烂碗,旧鞋底,甚至一把麦秆儿,也能换来称心如意的糖人儿。这里是孩子们的天地,大人在旁,也从不多嘴,一任孩子选择。男孩子多是要“猴抡棍”。只见老翁用锅中的圆木棍儿:挑_块黏糊糊的糖来,放在手中搓来搓去,倏忽便成猴之雏型,再精雕细刻,刀剪齐上,末了,屁股上竖插一竹棍儿,肩上平穿一麦秆儿,再往其孔中过一细竹瓤儿,两边反向弯成九十度,尖头贴一小圆糖。成了,拿在手中一摇,猴抡棍之式活灵活现。女孩子则多是“老鼠顶石头”。开始,只见老翁取一大块糖弄来弄去,似乎要做个很大的老鼠。孩子窃喜,以为玩过了吃糖也是便宜的。谁知这时,又见老翁双手各执一头,慢慢拉长,_越拉越细,屏住呼吸,气运丹田,直到老翁认为最好的时候,这才一边举起,一边吊空,那空着的手去轻轻一弹:掉在锅里的是四分之三,手中仅剩一点,孩子们都笑了,老翁也笑了。然后,他把那细头放在口中,口在吹,手在弄:老鼠的肚子鼓了,头也现了,两只耳朵尖尖的,嘴巴也出来了。再取一糖粒,置于鼠头,再吹,“石头”也出来了。栩栩如生,形象逼真,乐得孩子们哈哈大笑,大人也忍俊不禁了。至于那人物头像,则多是实心:拈一糖块,放在模内,压实,再取来麦秆贴上一提就行了;而较多复杂的三战虎牢关,醉打蒋门神,则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也非三分五分所能买到。
年底年初,老翁的糖人儿摊前是再热闹不过的了。在城里工作的人都回来了,于是,孩子们便少不了拉他们到糖人摊前。这个喊叔叔,那个叫姑姑,什么没过门的婶婶和未结婚的“姑夫”,也被他们统统叫来了。那些平日里从父母那儿索不来钱,抑或家里能换的什物早已换光了的孩子们,这时便会缠来比其他孩子更好的糖人儿。尽管,,他们的父母在一遍一遍地骂着“人来疯”,或者掏出腰包,给孩子摸出几分零钱,再在额头上戳一下:“咱等晚上着!”但孩子却全然不顾——能欢乐时且欢乐,过后挨打怕什么!这个时候,也是老翁最高兴的时候。他会看到:那位多年前穿着开裆裤,一天到晚围在他摊前的铁蛋,竟成了“解放军叔叔”,那位为换糖人儿偷了他爹尚能穿的鞋,挨了打还没吃上糖的二柱,也当上了工人,那个剪了自己头发换糖人儿,被她妈痛打一顿的芳芳,架上琥珀眼镜当上了教师;还有那不知叫啥名儿的小伙子,正挎着位“时髦”,在指着老翁讲他小时候弄糖人儿的故事……这时,老翁脸上便绽开了花。在大家的问候声中,说:“老了,快到那冬暖夏凉的地方(指坟墓)去了。”
我小的时候,父亲在城里工作,妈妈手头多少宽绰些,这就使我有更优越的条件弄糖人儿。皮球可以不玩,饭菜可以不吃,而糖人儿却不能不弄。锣一响,准到;人去摊散,还乐而忘归。妈妈也在摊前,我挑选,她出钱,花几分钱买孩子个笑脸,妈妈是从不吝啬的。按妈妈的想法,玩玩而已,吃糖为本,玩着痛快,吃着有味,老人们总是讲求实惠啊!而我,却不这样想,一来总是“猴抡棍”。久而久之,那老翁竟认识了我,我一到,他准会笑眯眯地说:“猴来了!”猴抡棍不知买过多少次,也不知化过多少次,老翁操作的全过程,我竟也了如指掌,成“猴”在胸了,闭着眼睛,我也做得来,只不过没有老翁做的好罢了。玩,也和其它孩子不同,总是把它插入炕边的砖缝内,早晚总要看来看去,每每梦中还在玩哩。为了不使它化,我睡的土炕从不要妈妈烧,更不要说生炉子了。有一年,竞放到三月初上,找高兴得半宵没睡,谁知一觉醒来,它却成了“流泪的红蜡烛”,我也哭成泪人儿了……
及至我高中毕业,回乡做了民办教师,还特别喜爱弄这玩意儿;不过,这时我的心绪已不在那“猴抡棍”、“老鼠顶石头”了——我让老翁做“蚂蚱吃辣椒”,置于桌上,插在瓶中。每每夜阑人静,我伏在案头备课时,便不时地瞟上一眼两眼:灯光下,辣椒是那样的鲜红红、活脱脱,嫩而欲滴,惹人爱怜;而蚂蚱,那翅膀一会儿是青的,一会儿是蓝的,一会儿又变成黄的。色调全凭灯光照耀,而又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着目,它后腿很长,略向后蹬,身子前倾,看上去真像刚跳上辣椒杆,立足未稳的样子;眼神,则是那样的专心、认真,甚至贪婪,竟不知“黄雀在后”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倦意全消,嗅着清新的墨香,认真备起课来……
关于糖人儿的记忆是很多的,关于老翁的事儿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有几回,凭着和他熟悉,我鼓起勇气问他,他却一个字也没透露。几年之后,才从旁人口中得知,老翁九十多岁了,他的手艺,是从他的爷爷,一位清朝同治年间的人手中得来的,捏糖人儿的,在那个时代,是被人瞧不起的,与乐人同类,和乞丐划一,媳妇自然是娶不上的。好在他爷爷曾在清廷干过事,娶下了他的奶奶,生下了他的父亲,而他,则是他父亲从一位要饭的手中买下的,时年十岁,契约上言明:买儿不在防老,无子亦非不孝,缘为继承祖业,使其发扬光大。
这一年,我考上了大学。四年后,分配到省上一个文物单位。报到之后,我赶回家里去——我要找到这位糖人老翁:黄金有价,糖人无价,而老翁,则是一个活宝啊!捏糖人是民间艺术,是祖国光辉灿烂文化的一部分,我要把这个瑰宝抢回来,留在我们的艺术宝库,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知道,他的祖先,曾有这样一种艺术样式。
然而迟了,待到我诚惶诚恐地来到这面土窑洞时,老翁已殁了。乡邻们告诉我,老翁仙逝在上一年的中秋。在那藕大如船,饼圆如月的夜晚,茕然无依的老翁,在秋风呜咽,灯影暗淡中去了。去时,老翁心里是很明白的,他说,几十年里,我走街串巷,逗乐了孩子,孩子们大了,却没有看得起这个行当。末了,他嘴里数十遍地念叨着:“和尚没儿孝子多,孝子多又顶什么?”
我哭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