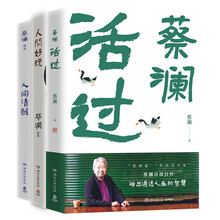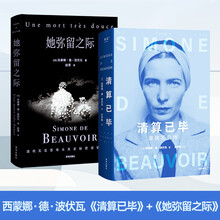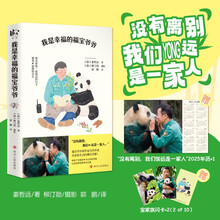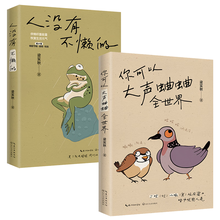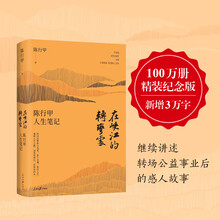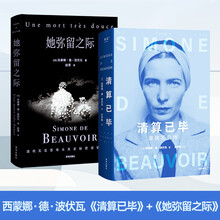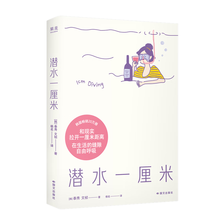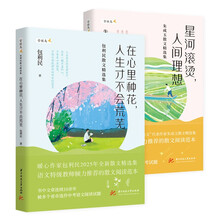杜诗异想录
臧克家
我从小喜爱古典诗歌,但只欣赏,不作研究。好读书,不求甚解,每诵古人诗,辄以个人创作甘苦印证、衡量,最不喜烦琐考据。诗词注释文友中,我颇爱冠英同志注的《唐诗选》、肖涤非同志注的《杜甫诗选》、陈迩冬同志注的《苏东坡词选》,都是个人研究的结论,以明净语句出之,平易亲切,专家、一般读者咸宜。
杜诗,是我所酷爱的,多年来,出游必携,如同良伴。经常置诸床头,灯下阅读。心领神会,其乐自知。但对版本的异同,注家的优劣,都茫茫然,甘居浅陋,不求深知。个人素不“强记”,况在老年?杜诗全集,虽读了多遍,但陌生者多,成诵者少。一字之奇,使我发出会心的微笑,对字句的体会也常以心作尺,不敢苟同于前人。
打开杜集,《望岳》冠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望岳》之前,即有所作,我们已经无缘看到了。对于这首杜甫的“少作”,几十年来,我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不论古今的注家,都认为是作者在远处或近处望泰岱而有作。我至今仍坚持自己这样一个见解:此诗是桂甫站’在泰山低处,如“斗母宫”上下,仰望高处的兴来之笔。这决非立意为高,强作解人,请以涛证诗。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这两个句子,都是写眼前景,并非抒心中情。“荡胸”一句,一般释为:望见山上云气层叠,故心胸为之开豁。我认为这样讲解,隔了一层。“决眦人归鸟”,我的体会是:作者站在山的低层,也许黄昏快降临了,望着平地上的鸟儿向山上的林木归来,状此景出之以“人”字。上句的“荡胸生层云”,有如“云傍马头生”,也只能是直感,而非借以抒怀。更令人启发的是结尾二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如果脚步连山麓也未踏上,何来“会当临绝顶”之思呢?那显得太突然,也太不合情理了。
除以诗证诗,还可以揣情酌理地想一想。杜甫写这首诗时,正是二十五岁的壮年,到了大名鼎鼎的五岳之尊,能失之交臂,仅仅站在远处遥望一下吗?我想,不但泰山庄严伟大的景象(如此诗开头四句所状写的)会引逗诗人一登临,秦始皇的无字碑、五大夫松,汉唐帝王登泰山、禅梁父的典实,也会鼓舞诗人一登的壮志。
当然,杜甫或因时间匆促,或因要事在身,或因健康有碍,或因……,这次没能登山“绝顶”,但有“会当”二字,不但表明了诗人的遗憾与希望,也表明了这次对于泰岳是涉足了的。
翻开杜集,凡是踏上高处的,都用“登”字。如《登兖州城楼》、《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登楼》、《登岳阳楼》等等。凡未登绝顶而小试脚步的,都标以“望”字。试以另一首《望岳》为例。这首与前一首,虽系所“望”的一是泰岳,一是华岳,但写作手法却是一致的。头四句描绘华l山高峻,五六二句状华山的险绝,请看结尾二句,与望泰岳何其相似乃尔:“稍待西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其源。”看他描缫近景,细咀通篇的意味,好似也是在山麓上走了一阶段,不仅是远远的遥望一下而已。否则,何必说等到秋冷之后,要登上险绝高处去呢?
最近,在《文史哲》上读到姜可瑜同志《也谈“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的长文,心有所感。十几年前,对这两个杜句的看法上,我支持了肖涤非同志。今天,仍然如此。上面说过,我最怕在注释方面搞繁琐考据,弄得字句未明,而诗味全消。道在近而求诸远,我觉得还是以诗证诗,更直接了当,更有说服力,也更简单明了一点。
开门见山,凭个人体会,这两句似应这么理解:“娇爱的儿女,怕我离开他们再远走了。”何所见而云然?
还是以诗中句,证诗中意吧。
《羌村三首》,整个情调是悲感动人的。诗人满怀抑郁,饱经忧患,历尽艰险,在离乱中死里逃生,得与家人团聚。真实的描写,心肝的披沥,亲人的叹息,邻里的歔欷,引起读者的共鸣,千百年后读之,仍感动不已。那时候,诗人的心绪是恶劣的,但同时又是欣慰的。乱世不幸的遭遇,如同一场噩梦,“相对如梦寐”,到底是“如”,而真的呢,是“生还偶然遂”的快慰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诗人虽然情绪不佳,但决也不会,板起一副冷面孔,使儿女为之生畏而离去。何况,既称“娇儿”,又“不离膝”,骨肉之亲,患难重逢,亲呢之态、之情可掬、可想。怎能反而“畏”而却走呢?更何况,从整个诗集中可以见出,杜甫是一个良夫,一个慈父。夫妇关系的和谐,诗人自有表现;对儿女一向娇惯,甚至到了“失学从儿懒”的地步。《北征》一诗中,与家人乍见面的那一大段描写,真是有声有色,感人至深!妻子儿女的情态生动影映在纸面上,深刻的印在我们心上。且引几句看看吧:“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竟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请问,这样一个慈父,在这样的环境里死别重逢,“绕膝娇儿”,亲还亲不够,怎能望而生“畏”,吓跑了呢?!
肖涤非同志,对杜甫研究功力湛深,我在“国立青岛大学”读书时,他教过我词学。以年岁论,我长于他,以“闻道”论,他先于我。文化大革命前,我写信给他称“先生”,接着加以解释“先生,非客气之称,尊师重道之谓也。”他回信大加反驳。以后在信上,我仍称“您”,他又来信批评道:“何必多此一心?”十几年来,你我相称,我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了。最近,他把《杜甫诗选注》赠了我一本,我经常阅读,划圈点点,连小注也一字不漏。涤非同志,学识渊博,足为我师。他的注释,语句无多,简明洁净,说得中肯,令我心折。虽然如此,但读了注本之后,我仍然有点自己的看法,现在顺便写出来,就正于涤非同志。涤非同志对杜诗极为欣赏,心心相印,我有同感。日本名记者青木来访时问我,对李白杜甫的看法,我回答说:“我觉得杜甫离我近,李白距我远。”评论人时,完全摒除偏爱,是不容易的,存心公正,也难免在字里行间流露个人的情绪。我觉得涤非同志在评价杜诗——特别是他晚期作品时,有将消极成分说成义愤的个别地方。在批评郭老《李白与杜甫》一书时,谈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用了大量考证,证明“寒士”即“人民”。我给他信说,这大可不必。杜甫虽然有过官职,但到晚年,也成“寒士”,连类而及,合乎情理,读者自会从“寒士”意许、推及到“人民”的。
还有,涤非同志对有的诗句,注曰:“含有十层意思。”我觉得这么讲,太玄,也有点学院气。蘅塘退士在《唐诗三百首》中,作了许多名句的旁注,说:有十几层意思,有二十层意思。我问:十九层行不行?两层三层行不行?我想,只说“含蓄耐人寻味”就行了,各人有各人的体会,难订十层二十层的框框。订了,读者还是要“逾矩”的。
另外,杜甫从成都到了夔府,写下了有名的《诸将》五首。末首起二句是:“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有的同志将“逐人”的“逐”字释作“驱逐”,我个人的体会,“逐”字应作“追”字解。诗人心中带着锦江春色来到了夔府,清秋时节,追忆老友,触及往事,有景有情,似乎更有诗意些。对于古人的诗句,见仁见智,各自不同,这是不免的。
选自《散文》1980年第2期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