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含冤三十多年之后,武训也总算得到了公开的平反了。
严格地说,还只是半平反,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平反。
有人干脆就不说“平反”,而只说是“纠左”。
“纠左”?谁的“左”?毛泽东。谁在纠?毛泽东当年的秘书胡乔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今天在这里否定了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他是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新华社这么说。据说,胡乔木指出,一九五一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不但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
尽管这两个“不能”说得有些吞吞吐吐,却还是被认为是对武训的否定之否定了。
事实上,这只是对《武训传》批判的否定,还不是直接为武训平反。当年武训被斥为“清朝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这三项大帽子还没有正式摘下来。
这三顶帽子——“奴才”、“对头”和“帮凶”是跟着一个“主义”而戴上的:“投降主义!”毛泽东在中南海看《武训传》时,吐出了这句话,未终场即去。也可以说是终场,他这一走,电影就放不下去,完了。
武训也就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跟着展开。主持其事者之一,就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尽管“犹抱琵琶”,今天由他来否定这一场批判,就多少有些自我批判的味道,尽管他没有提到当年自己如何如何,这也许由于并不是在作“全面的评价”的缘故吧。
陶行知也就完了。由于他生前推崇武训的办学精神,也可以说他就是有着“武训精神”的教育实践家。自从《武训传》挨批,死去了的陶行知也就三十多年抬不起头来,他也就成了连带被否定的人物,武训的异代连坐犯。这也正是为什么胡乔木要在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的时刻,来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的缘故。
其实,第一个半公开为武训平反的,不是胡乔木,而是万里。万里也不是在一九八五年六月和老同学张绍虞谈话时,才为武训平反,这场谈话一开始他就说:“我已经在全国教育会议上两次给他平了反嘛。”(见《明报月刊》一九八五年十月号《武训平反问题三文件》)。这个“已经”,不是一九八五,而是一九八四。按说,在有关会议的文件上有记录,不过一般人看不到,因此只能算是半公开的平反。
万里的半公开,不等于胡乔木的半遮面。他是毫不转弯抹角地说,不能把武训称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农民阶级的投降派”的。而且,他毫不含糊地说,要平反。虽然不知道他还具体说了些什么,比起胡乔木的话来,他是快人快语了。
虽然是快语(万里)和不够爽快之语(胡乔木),都了无诗意。
但不可不知,胡乔木却是个诗人,正和毛泽东是诗人一样。
不“全面评价”对《武训传》批判的他,在诗词的创作上,是比毛泽东更全面的。他不仅写旧体的诗词,还写新体的诗,简称新诗的诗。他不仅采用中国古典诗词的格律,写新体诗时,还用西洋诗的格律。
记得在“文革”以前,《红旗》杂志曾经用过整整一两页的篇幅,刊出他好些首词,都是格律谨严的,其中有咏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霹雳一声春,风流天下闻”的句子;也有咏西湖边上拆掉那些伪托的古代英雄美人墓的“如此荒唐”的句子。
这两年,地位高了,他的旧体诗更在《人民日报》主要的版面、显著的地位,新闻般地刊出了;而副刊上,就刊出他的白话新诗。
据说,他在爱写旧体诗的胡绳处看到香港出的聂绀弩的旧体诗《三草》,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意出新的补充修订本。就主动上门,拜访病榻上的这位老诗人,又主动表示要替这一《散宜生诗》写序,在序中赞扬这是“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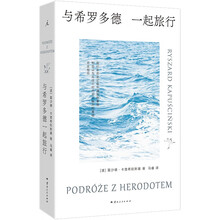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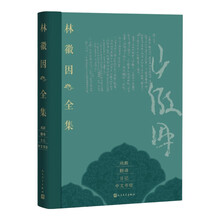
——聂绀弩赠罗孚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