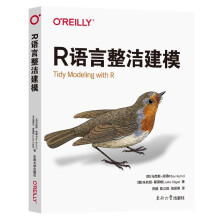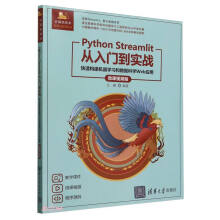第二节 结构与论点
本书主体的框架结构主要分为三大板块:历史话语篇、历史文本篇、诗学形态篇。基本论点如下:
尽管渗透了“文学性”的历史古已有之,但20世纪的知识谱系使“文学性”和“历史性”分别成为文学和历史的专有属性,因而“文学性”与“历史性”在学科分类的知识格局和科学视野中曾走向对立。从“文学性”而言,诸多论者都曾将“文学性”问题归结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如乔纳森·卡勒就提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可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一是“关于文学的一般性质”;二是“文学与其他活动的区别”①。这一理解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论者在众多话语中寻求文学独立地盘的努力。以“历史性”而论,即使是反对史学中的自然科学或实证主义思潮的柯林武德也指出:“一门科学与另一门科学不同,在于它要把另一类不同的事物弄明白。历史学要弄明白的是哪一类事物呢?我的答案是resgestae[活动事迹]:即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②这一论析同样可以看到历史专业研究者对历史事实的“圈地运动”。
而有趣的是,学术史又进入了新的轮回——随着“语言学的转向”,“意义本体论”受到严峻挑战,语言活动与实际世界的指称关系被割断而走向反本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以形象的描述为“文学性”与“历史性”的通约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撑,使“文学性”与“历史性”从冲突走向融合。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中译本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随着19世纪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
于是,“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社会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总之,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①。而且,“坚持让社会科学朝着兼收并蓄的方向发展(从学者的来源、对多种文化经验的开放性、合法研究主题的范围等方面来说),这能够增进获取更客观的知识的可能性”②。因此,海登·怀特主导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历史哲学领域中的语言学转向,并将历史主义思想带入文学批评领域,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海登·怀特自信地宣言,史学家对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③;“文学性”决非限制了“历史学家的身份”,“恰恰是他们话语中的这种艺术或文学成分”“巩固了他们作为‘经典’历史作家的地位”④。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