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去世前不久,我被送到科罗日瓦和祖父、姑姑住在一起,父亲和祖母则留在家照看母亲。一天早上,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
就在当天下午,我们收到了一份电报,接着,姑姑告诉我马上回马吉他,因为母亲的病情恶化了。当晚,那列唯一的火车停在了距离马吉他不远的几站外。所有的商铺都关门了,那冰冷、覆盖着厚厚的灰尘的候车室显得比以往更加阴沉。我躺在一条长椅上,紧张得睡不着觉,姑姑告诉我,母亲其实在早上就已经去世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不停地哭泣、瞌睡着。黎明时,我们裹上了粗糙的毛毯,乘坐一架马拉雪橇回到了家。那是1942年1月。
我们回到家时,父亲正等着我们,他满脸胡须,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所有犹太人哀悼者那样深折着衣领。“现在就剩我们了。”我父亲说。
当他亲吻我的时候,杂乱的胡须刺痛了我的脸颊。而他向我重复母亲的遗言时,他哭泣了起来。“我很好,”母亲临死时对父亲说,“但你们还要面对艰难的日子。”不一会儿,我母亲哭喊了起来,“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然后便死了。很快,母亲的遗言便得到了验证——或者那只是她冷静的远见。
根据犹太习俗,我们回家后母亲便被下葬了。在她的墓前,我背诵着珈底什(犹太教为死者祈祷时唱的赞美诗)。如今,我已经不记得其他人都做了什么事,但我清楚地记得,我独自在墓地旁的山坡上坐了一整天。
母亲去世多年后,有人告诉我,我曾经不愿意和母亲说话。事实上,我不知道要和她说什么,因为我一直不了解她。在对她不多的记忆中,我记得她最喜欢的两首曲子是托斯卡的《群星闪耀》和皮尔金的《索尔维格之歌》。也许她本质上是一个忧郁的人,不过我父亲经常表扬她是一个机智、镇静的人。两件事可以见证父亲对她的评价。
一次是在母亲生病时。母亲咳嗽得特别厉害,于是父亲请来了两位医生,其中一个医生在床边对另一个医生说:“她快不行了。”母亲缓过气来后说:“哦,医生,我还活着呢,是吗?”那是最后一次有医生在她的床边做出这样的预测。另一次是在母亲与一个小偷搏斗时。母亲总是将一根吸管放在枕边,接下来的场景就像一场闹剧一般——她用吸管猛地将苏打水喷到了那个闯入者的脸上。小偷骂了几句,接着便仓皇而逃。无论那个小偷多么镇静,都无法敌得过结核杆菌。
在母亲生病期间,父亲总是雇用一些当地农妇来做家务。而母亲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小姨莎莉经常会过来陪我们。对我来说,她既像我的姐姐,又像我的第二个母亲。我记得,她不仅将我带到河边,教我游泳,还带我到当地电影院看电影,让我认识了电影中的泰山、劳雷尔、哈代,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中的贝蒂·戴维斯与埃罗尔·弗林。我们还观看了赞颂英勇的长枪党人为保卫托莱多城堡而与共和党人激战的西班牙内战史诗和《大力水手》。看电影时,我们会嗑一些瓜子,能将瓜子放在嘴里而不用手就可以吐出瓜子皮是当时我最引以为豪的事。我的小姨是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一员,曾被罗纳尼亚和匈牙利警察逮捕并多次严刑逼问,但从未透露过半点秘密。后来,出于对父母的孝顺,她错过了躲避大屠杀的机会。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37岁了。19岁时的他结束四年的中学生活不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便志愿参加了奥匈帝国的军队。他的朋友们劝他受点轻伤、手臂上扎上绷带回到维也纳或布达佩斯,因为那里的女孩疯狂地追捧勇敢的士兵。事实上,他的膝盖真的被一颗在《国际法》中是被禁止使用的即达姆弹击中了。接着,他在一片沼地上躺了几天,最后被送到了维也纳的军事医院。父亲没有将手臂用绷带吊起来,身后也没有女孩的追捧。相反,他永远地失去了膝盖骨,带着那条僵腿和一根拐棍度过了余生。庆幸的是,30年后,那颗达姆雷弹头被证明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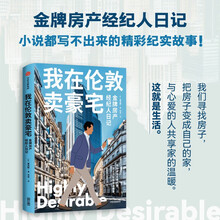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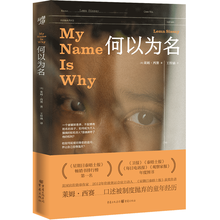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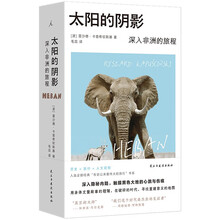

——英国著名学者 克里斯蒂安·阿格瓦瑞
勒布的故事有时甚至是令人心碎的……它充满感情地讲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卡斯特纳是二战期间拯救犹太人最多的人,历史却没有完全承认这一功绩。
——英国《周日商业邮报》
或许是大屠杀幸存者的缘故吧,拉斯洛·勒布的书注定和其他相关题材的作品不同,更加真实,更有感情,也不失事实依据。
——约翰·卢卡奇《纽约书评》
二战是全世界的灾难,对匈牙利的犹太人来说更是如此,感谢拉斯洛·勒布教授公正地告诉了我们历史的真相。
——《匈牙利民族报》
拉斯洛·勒布为人严谨,而本书还原了历史真相,并借鉴了大量的史书,可以作为二战时期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法国《自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