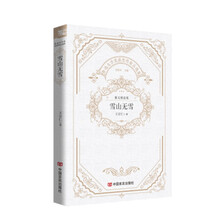作者把比利写成一个“正直的野蛮人”,把纳尔逊上将说成是比诗人更伟大的感召者,把威尔船长视为谨醇克己的精神贵族,目的是为现时代普遍的精神堕落提供批判性对照,在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绘制一份道德谱系,并使之贯穿一种强硬的道德训诫。作者对于不同人格内涵的揭示,显然不只是为了服务于故事的界面。例如,格雷弗林船长是个次要人物,在第一章中出现后便消失不见了,作者同样以生花妙笔给他制作素描,并以柔情的幽默描绘这个“聪慧仁慈”的人物。事实上,麦尔维尔对于海上社会并不抱有浪漫化的想法,他将战舰的警察系统与陆地的商业部门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与“全体的道德意志相违背”,但是只要涉及人类道德风范及其消亡之中的纯真质朴的魅力,他会不惜笔墨,将誉美之词奉送给帆船时代的水手,并以高调的姿态对陆地文明社会做出冷峻的评判。麦尔维尔的海上道德哲学,后来在康拉德的同类创作中显然是有所呼应。麦尔维尔是美国人,康拉德是波兰人,他们对大英帝国帆船时代的海军和商船水手怀有淳朴的景仰之情,根据这个光荣的群体来设计那些具有道德魅力的人物,这种做法能够反映他们的价值观。
《比利·巴德》其实是一部外国题材的小说,写的是英国海军的故事,为什么查尔斯·瑞克说它表达的是“对美国命运的悲观看法”?因为美国是新兴的商业文明和现代价值观念的代表。身为美国人,作者的立场和视野必然影响他对题材的思考,而他的思考确实是溢出了故事的界面,使得小说的叙述也包含诗人对于现代文明的反思。
纳尔逊的“胜利号”残骸与欧洲庞大的铁甲舰,英吉利海峡的战争与巴士底狱倒塌的“斗乱烟尘”,革命时期那种“异教徒的大胆放肆”与欧洲时局的动荡不安,这幅宏观的历史图景意味着价值的变革,也意味着价值的深刻危机;作家并没有被“人的权利”及其进步的表象所迷惑,而是对这个世界的进程抱有微漠深广的忧虑。篇中但凡涉及法国革命、拿破仑及“恐怖时期”的督政府,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的评价。作者批评英国海军的“强行征募”政策,对“诺尔哗变”做出中肯分析,但总体上还是将英国海军的危机与欧陆革命的动荡联系起来,强调旧秩序的崩溃所带来的各种恶果。他的同情是落在英国人这一边,仿佛这个岛国象征的体制和道德感处在孤立的境地,被革命的火焰和地狱魔影所包围。麦尔维尔遗作中这种保守的思想、立场,影响到这个故事的讲述。他坚守贵族荣誉感和自觉的道德激情,这种思想贯穿于各类离题话的敷衍阐述当中,也体现在纳尔逊上将、威尔船长和格雷弗林船长这些形象的刻画之中。
中心人物当然还是威尔船长。一个斯多亚式的精神贵族。他不像“英俊水手”或纳尔逊上将那样熠熠闪亮;他的面目是要平凡得多,但他的人格当中有着一个令人着迷的跨度,从军人的严肃干练到耽于沉思的书卷气,使他的形象散发独特魅力。威尔船长其实就是那种父性权威,凝聚着种族的精血和理性,而一个没有父性权威的种族则是破落混乱的,会纠缠于怨恨而丧失希望。我们不应该将他对于信念、秩序和形式尺度的看法,仅仅理解为刻板的军纪训导或书生气的迂腐,而是应该理解为对于价值失范时代做出的敏锐修正。小说第六、七章制作的两幅素描,可以帮助我们去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那种斯多亚式的超然与内威的微妙反差,有着造型上的坚实内敛的美感。
麦尔维尔是一位小说大师,对于人物的精神等级有准确的把握。他并没有去美化普通群众的精神面貌,也未借助于罗曼司和通俗剧的情欲渲染。他想探究人性恶在道德生活中的位置,而不是要去绘制一个平面化的地狱。小说是典型的19世纪作品,保留着性格鉴赏的趣味。它不像今天的小说,由于价值的过度分解而趋向于琐碎暖昧,而是根据反思的张力来设计人物,将人物形象与道德思考的内在活力结合起来。谈到威尔船长,如果说此人只是一个实施纪律者,并不具备深沉的人格魅力,如《导言》作者所说,不过是“一个蹩脚的纳尔逊”,那么比利的审判恐怕也不至于如此让人思索。换言之,对威尔船长轻易做出贬抑性的评论,其实会削弱这出悲剧的力度。
五
其四,关于比利的审判。具有父性权威的英明的威尔船长,在关键时刻抛弃了比利,这只最需要他保护的羔羊。是他组织并操纵战地临时军事法庭,将比利送上了绞刑架,因此在读者心目中,他的行为无异于谋杀,做了克腊加特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如果说比利的悲剧是代表“正义和法律的冲突”,那么威尔船长至少没有站在正义这一方。他成了法律冷酷无情的代表,他的判决是对纯真无辜的谋杀。
比利的审判是小说的高潮,有关庭审的章节也是此书篇幅最长的章节。读者关心的是,判决能否有另外的结果?也就是说,比利能否不死?根据《军律》和《反叛乱条例》,比利虐杀上级,理当处死。将此案移交舰队司令员来处理,结果怕也一样。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