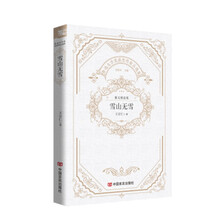我看着他,一张年轻的脸,纯真的表情,上等兵军衔,浑身的疲惫。他开口说话,嗓子有些哑,语气很急促,夹杂着喘息,白色的雾气在嘴边萦绕,生生不息,如燃得旺盛的火苗。他喘气,好似要把心喘出来。他说,才走了十几公里,今天可能要到晚上才能巡完。我不慌不忙,用手拍了拍他的肩,静心等待,给他足够的时间平息负荷的心脏。我看见他还背着一个军用水壶,前后摆动的水壶似乎在大声喊,渴。我敢肯定,那里边的水早干了。高海拔,稀氧气,低气压,对水的需求太大了。人的皮肉、骨骼、血液,哪一样能少得了水呢。他望着我,等待我的吩咐。每遇这样的情况,我都不做声,感到话语多余,感到有些话说出来就是虚伪。他的脸有些发青,可能是走得太急的缘故。据科学测定,海拔每上升100米,大气压强就降低0.7千帕。事实上,压在他身上的,不只是一把锹,还有无形中的力量,那是自然强加的,是所有来到这片荒原上的人都要直面的。我只看到他一人,其余的人可能正巡到了山的另一边,大多时候,他们透支体力,大海捞针般寻找,为的是避免损失,减少浪费,维护一种正义。<br> 这些年,在漫长的青藏线,我总能遇见一些孤单的身影。可可西里无人区、长江源地区、藏北草原……我的目光无一例外在他们身上停留。他们很孤单,寂寞,还有一些少年的幻想和伤感。有一些人在孤单中完成服役期就回到了故乡,而有的人则在孤单中成长为老兵,还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走出了一身的病。长期在低气压的环境下工作,容易导致内脏器官发生各种病变,肝大、心大、肺大、小脑萎缩。大高原如同酒鬼,醉酒后又有许多的恶习。这些战士全都来自内地,他们在地球的头颅上,挖掘沟渠,铺设管线,维修机械,烧水发电,值班输油。野外巡线是最不起眼的杂事,因为没有技术含量,或者还因为谁都可以干这活,原因是简单。简单的事情,有时也是繁重的事情。同一片天空下,这里的紫外线辐射强度高出内地6倍以上,经常在阳光下照射,会对皮肤造成严重灼伤。每次面对紫红色的脸庞、干裂的嘴唇,我都会想起风雪中孤独的身影。每年280天的冰冻期,年平均气温-6℃,最低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这里是最不适宜人生存的地方,但还是有人生活了下来,且一年又一年。遥远的路途,最常遇到的7级以上的大风,每年刮120多天,飞沙走石、遮天蔽日。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三人,青藏线经过的可可西里地区和西藏羌塘草原北部都属“无人区”,数百公里都看不到一个人影。可能年轻,没有人向高原妥协,连初来乍到的怀疑和隐隐的恐惧都没了,那些东西像雾像雨又像风,越近越清晰越是不怕。因为不怕,人才能攀山越岭、蹬冰过河,走更远的路。<br> 现在,我身边就站着一个这样的战士。他不跟我对视,只望着远方。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远方总有无穷的诱惑力。我知道,他惦记着没有巡完的路程,要不然,会受到嘲讽的,当过兵的人知道,部队有褒奖勇者和鄙视懦夫的传统。我问,天黑前能不能巡完。他说,没问题。很干脆,很自信。自信也是战斗力。我接着说,你去忙吧。他应了声,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一颠一颠地走向了荒漠。他有着一张孩子的脸,望着背影,我有些难过,但毫无办法。他的身影模糊时,我才蓦然想起,他的水壶里没有了水,等待他的,只有忍耐。恶劣自然环境容不得你不去吃大苦耐大劳。<br> 为了站得高些,他们来到高原,意外的是,他们没想到还要走那么远的路。一个人一生能走多远,恐怕没人说得清,但一个人竭尽一生的时光,肯定走不完脚下的路。那具孤单的身影,双腿沉重而疲惫,在寸草不生的荒原中一点点矮小,最后,风一样隐没。我打扰了一个正在聚精会神忙本职工作的战士,心中升腾起一丝愧意。<br> 再次前行,空茫的眼中,就浮现出许多寂寞的身影。我不知道,在遥远而没有尽头的征途,他们可有过从军的失望和悔意,会不会为枯燥的日子匪夷所思。<br> 我在这世界海拔最高、氧气最少、阳光最暴烈的地方,看到了许多无法叙说清的事情,每当我静默,有些事便如蛇一样从隐蔽的洞穴中探出头,然后再滑出冰凉身体,徐徐前进,一有风吹草动,迅速逃遁。蛇行无迹,但它真的在我心头来回穿梭。车轮碾轧路面的声音不绝于耳,除此,天地一片死寂,山没有一丝的绿,高原把所有的山都变成了同一类型,光着脑门,皮肤粗糙,门牙脱落,越是往上走,越是有往棺材里钻的沮丧。<br> 阳光惨烈,斜挂天穹。我让车停下,跳下车来,抬起头,蓝天如一面宝镜,光洁而平滑。山坡上,一个人影站了起来,如不起身,让人疑心是块石头,他朝我张望,撞上我的目光后,他激动地抬起了手臂,然后朝我跑来,那个军礼如一股春风拂面而过。我握了一下他的手,皲裂冰凉,嘴唇上有血痂,乌紫暗红。他站在我面前,身体笔直,不说话,不看我,而是看没有风景的山。他的行为、举止、细枝末节,外化为一种特有的气质,浑身溢满了不气馁不服输的劲头。冷冷的气流,无法掩去他的积极和乐观。我问,坐在山坡上干啥。他说,巡完了,等人,黄文强。我看他刚才坐的地方,那儿竖起了一把铁锹,倒着栽插,像是一个静立远眺的人。巡线时,战士们一般采用一人一段路程相向而巡,有的快有的慢,通常,碰上面后再结伴到公路边,等营部的收容车。我不知,战士们为何不敢与我对视,他们游离的目光来回跳跃,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撂给我的,大多是一个侧影,我想,这可能是长时间与山对峙的习惯。我甚至不忍离去,把他一个人扔在荒原,那么灰黄暗淡,那么脆弱渺小,养成这样的习惯,需要多长时间来完成?<br> 每年,我都有段时间作别高原到内地休假,每次融入喧嚣与嘈杂的环境,会涌起说不清的倦意,会有说不清的孤独。我年轻而不谙世事时,觉得人是多么了不起,人的双眼,可以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人粗壮的骨骼能焕发出巨大的魔力,那树桩一样的两条腿,总是超出了我思维无法达到的跨越,我差点坚信,人是天地最伟大的神灵。然而,我多年的高原生活后,在厚重的原始环境里,我发现人其实尘埃般微小渺茫,那维系种族繁衍不息的生命在很多时候脆弱不堪。认识到这一点,我莫名兴奋,比拾到受用不尽的钱财更庆幸,感到孤单也是一种幸运,因为对人来说,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哪怕是受些委屈,遭遇厄运,这些算得了什么呢?<br> 冰冻的气流中,我的心炙热起来。<br> 对于战士们的巡线生活,我是熟悉的,他们在阳光和风雪中寻找,眼睛圆睁,像鹰。身上散发的汗味和没有表情的面孔,时不时就在面前显现,当然,还有不同凡响的作为,他们对着太阳放肆地撒尿,有点沾沾自喜,头脑中古怪的想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对着大山唱歌,五音不全还自我陶醉;对着河流大喊自己的名字,喊上一阵就哈哈狂笑;也有对着电线杆背诗的,全不顾遇到的是白痴,不解风情。真实,自然,是他们的态度,也是种别样的表达,没有人走进他们的内心,在几乎被遗忘的岁月里,他们把枯燥的生活变得生动有趣。同样一身军装,他们与大多身着军装的人是多么与众不同。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