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的7毫米
By 浅白色
很多不起眼的东西都是这样,
在明明有迹可循的记忆里完美地消失了踪影。
从束河回来后,我的眼药水不见了。
我明明记得从客栈离开前曾将它收在化妆包里。那一刻,它迅速而干脆地跳落在护手霜和睫毛膏的缝隙之间,安然卡住,一动不动,深绿色透明瓶身里的液体微微晃荡,撞出一些瞬间就破裂的小水泡,很快平静下去。我拉上拉链,将它装进包里。化妆包并不坚硬的皮质表层被钱包、手机和钥匙挤出了凹凸的纹路。
收拾好行李,我从电视柜旁边拿起房间钥匙,这才退房离开。这一段回忆相当清晰。再往后想,却记不起路上数次打开化妆包时,那个深绿色的透明小瓶是不是还在原位——最后一次,是在回家的出租车上。车已经开到小区门口,我手背上还停留着刚刚挤出来的一团指甲盖大小的护手霜。黎靖见状接过护手霜瓶子替我装进化妆包,打开车门下车,径自去抬后备箱的盖。
车门外是十二月的北京。
等到我钻出车厢,他将旅行包的拉杆长度调好,递到我手上,说:“进去吧。”
我接过拉杆,目送他坐回车里,一时恍惚,忘记要进小区大门。
出租车缓慢地向后退去,寻找合适的方向原路离开。他在后排摇下车窗,对我挥手:“赶快进去吧!”他的声音终于渐渐消失在引擎声里,车子退出了我的视线范围。暮霭渐渐下沉,厚薄不均的雾气让视野时而模糊时而清晰。行李包底端的小滚轮划过地面发出有节奏的声响,面前这幢高楼里密密麻麻地亮起了灯光。
我以为这种旅行结束的感觉会发生在走出机舱的那一刻,原来这一段路才是旅程的真正结尾。
工作四年多,我一直没有长途旅行过。
如果不是因为黎靖,就连这唯一的一次也不会有。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频繁地回忆自己做某一个动作时的情景。有时是因为记不清楚将某样东西放在了哪里,有时是无法确定自己究竟是否曾经做过某件事。
这一年,几乎每天清晨在呼啸的地铁车厢里,我都反复回忆出门前自己有没有关洗手间的灯。那些记忆并不会因为反复追溯而变得清晰,反而越来越模棱两可。像是有过,又像是没有过。
在回到北京的这个傍晚,我因为找不到眼药水,开始陷入再一次的反复回忆。一次又一次,回忆收拾行李从束河的客栈离开,到丽江,再上飞机……
很多不起眼的东西都是这样,在明明有迹可循的记忆里完美地消失了踪影。
在身后这张宽度一米五的双人床上,黎靖常常头枕着我的腿,用大拇指和食指撑开自己的眼睑,等我帮他滴眼药水。厚窗帘背面是渐渐浓起来的夜色,墙边银灰色的暖气片锈迹斑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发热。黎靖已经搬走。还剩下十一天,我也必须搬离这间屋子。
在这样一座城市里,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下一个容身之所。在一起,不仅代表爱,还代表共同生存的需要;不愿意分开,不仅代表不舍,还代表惧怕从此无依无靠,孤独地面对喧闹的世界。
当爱与生存变成不可分割的同一个命题,你会开始发现很多曾经泾渭分明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
这一切你都无法真正拥有,区别只是你是否以为自己曾拥有过;每样东西都有有效期限,区别只是你知道或不知道到期的日子是哪一天。
黎靖是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时的同事。当时他是个小企划,我是个小翻译。在那家公司两年,我们仅有的交情只是见面打个招呼,除了姓名和部门以外对对方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不是一年前有个旧同事移民,而我跟黎靖恰好都被邀请参加聚会,我们永远都不会再有联系。
那天吃饭他坐在我左边,聊了什么已经记不清楚,在模糊的印象里只不过是一个单身女人和一个单身男人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彼此在那一瞬间都很庆幸不用再孤单下去。我们迅速进入了状态,经常聊天,约会,很快住在一起。
我们都只是独自生活在北京的平凡男女,生活是快速又毫无意义的循环,即使曾经期待过爱情会以某种姿势来临,却根本不可能分出为生存而战斗的时间来慢慢体验爱。对于我们来说,目前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爱,不过是在清晨有另一个人跟自己手拉手挤上同一趟地铁,在傍晚有另一个人跟自己握着同一把钥匙,打开同一扇门。
我们将租来的房子称为“家”,像小动物一样轻易而单纯地互相取暖,毫无保留。爱情就是这样一件温暖又实在的小事,让彼此不再孤立无援。
其实,一直到今天我都在疑惑:爱的产生究竟有没有必要条件?
我们搬进这套小公寓的时候也是冬天。北京打破了一百一十天没有降雨的记录,终于在冬天的尾巴上微微湿润起来。
小公寓楼层不高,但卧室有一面大玻璃窗。搬进来的第一天下午,黎靖爬上窗台装窗帘。他整个人几乎贴在玻璃上,小心地挪动脚步,抬着手将窗帘挂钩一个一个卡进轨道里。我站在一旁抱起悬挂下来的窗帘布,避免他踩到后被绊倒。那一刻,我看到他的裤缝干净地直立着,有雨点隔着玻璃停在窗上,像一个又一个发光的小晶体,静默在黄昏的光线中。
那一天的雨下得并不大。
晚饭后,我们捧着水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虽然我们都早已没有看电视的习惯,但总觉得这样的情景才最有家的感觉。
新闻正在播今天这场小雨:“下午1时左右,北京市主城区内均下起了零星小雨,北京持续一百一十天没有降雨的记录终于结束。气象专家表示,北京气象部门的人工影响天气部门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做好人工增雨的准备,希望能够抓住这次机会成功作业。
数据显示,北京自2008年10月24日以来,一直没有出现明显降水,在此期间,北京平原地区平均降水量仅为1.1毫米,比常年显著偏少,处于自1951年以来的第二位……”
黎靖转过头问我:“你知不知道降雨量是怎么算的?”
我摇摇头。
“想不想自己量量?”他对我眨眨眼。
“难道你会量?”
他把杯子放到茶几上,沿着杯口上方画了个圈:“很简单的,先找一个罐,在里面放一个玻璃瓶,然后用一个直径20厘米的塑料碗或者纸碗——有些泡面碗就可以,在碗底中间钻个USB口那么大小的洞,把纸碗放在上面,碗底的洞正对着罐里的玻璃瓶,雨量筒就做好了。把它放在离地面高70厘米的地方接雨水,等到雨停,取回来称一称瓶子里的水量就知道了,每30克水相当于1毫米降雨量。”他双手一直比划构成量雨器的每一件容器的形状,兴奋得像在规划属于自己的房子一样。
我问:“既然碗底要挖洞把雨水漏下去,为什么还要规定直径?”
“这个问题你应该反过来问:既然要规定直径,为什么还要挖洞把雨水漏下去?”
“是啊,为什么?”
“一般的直径20厘米雨量筒,上面是漏斗,底下的量杯直径是4厘米,有刻度。现在自制量雨器必须钻个洞代替漏斗,而且一定要是圆柱型,还要求有一定的高度,不然稍微大一点的雨滴落下来会把筒里的水溅出去。明不明白?”这次,他把双手张开,做出捧住一个圆筒的姿势。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的?”我喜欢看他向我讲解问题时候的样子。
“我上初中的时候就知道了,地理老师教的。怎么样,要不要量一量?”他故作不在意,语气里有种孩子的得意。
我站起身钻到窗帘后,看了看已经彻底黑下来的天,玻璃上不再有雨珠:“雨都停了你才告诉我。”
“不要紧,下次泡面吃记得把碗留着就行了。洗干净,钻个洞,搁到罐子上,等下雨天就放出去。”
“说得这么容易,你做过几次?”
“我?”他显然没料到我会问这个问题,“初中做过几次吧。有什么问题?”
“这么多年了你都还记得怎么做?”我很好奇。
他背靠着沙发,伸手把我拉过去躺在他肩膀上。我的头发垂在他颈边,痒得他不自觉地缩了缩:“当然记得了,当年我还立志大学要学气象,结果因为高中成绩太好,被保送了。高考当然是能逃就逃,所以我糊里糊涂学了四年物流,毕业后居然做了这么多年市场。你呢?”
“我什么?”我抬头看他,额前的头发蹭着他的下巴。
“你以前有什么理想啊,还有为什么会来北京被我遇到?”
“我没什么具体的理想,就是很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其实经历过了也就发现不过如此,工作几年,觉得有点厌倦,但又好像根本停不下来。觉得这种忙碌的状态早就已经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像现在这样过下去,根本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能让我生存下去。”
我学的是语言。毕业后一直做笔译,三年来从半大不小的贸易公司到留学中介机构,每天的工作都是按照固定的模板翻译各种函电和文档。上大学时接触的专有名词是莎士比亚玫瑰战争工业革命,做翻译后需要用两种语言准确地知道碳酸氢钠和汽车发动机冲程。积累了工作经验的同时发觉自己整个人生越来越空,越来越窄,就快要没有选择的余地。
“你就真的没有过理想?”他难以置信地问我。
“其实以前也有过,刚实习那会儿总是想:等我拿到工作第一年的年终奖就出去旅行,至少要去超过两千公里以外的地方才算是旅行。结果工作之后根本不想旅行,时间已经走得太快,我跟都跟不上,哪还有精力那么辛苦地往外跑?而且,有多余的钱不如存起来,万一哪天房子出了问题,或者突然失业还能支持一段时间……”
听到这里,他摇摇头,伸手轻拍我的额头:“这么说来你真是太亏了,既没旅行,又没真正存钱。”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越想存钱就越容易月光。乱花钱觉得罪恶,但忍着不花又太对不起自己了。别说存钱,现在咱们俩付这半年房租加押金和中介费,连信用卡都全提现了,现在是欠着银行的钱生活……”我的额头顶着他的下巴,放心地跟他抱怨我们的经济危机。
一个人的时候,存钱是种带着惊恐的强迫症:万一失业,万一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万一……而在那一刻,我心里毫无恐惧。反而有种相依为命的幸福感。
只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明白,这种幸福感到底是互相依赖还是爱。或许在此时此刻,两者没有任何分别。一旦我们不再需要为生活担忧,会不会显露出这段关系除了相依为命之外的本来面貌?
黎靖拍拍我的背,让我坐直身体,转过来看着他。他说:“谢珣,放心吧,今年我一定带你去旅行。”
“真的?”我笑了笑,“我们还是还完信用卡再说吧!估计等还得差不多的时候,又该开始存下半年的房租了。”
“喂,你太没情趣了,也对我们太没信心了吧!等着瞧吧,我说到做到,今年一定带你去旅行!”他伸出手来点我的鼻子。
十一个月后,我们终于决定一起旅行。
这是四年来我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如果不是因为黎靖,它或许永远不会发生。
如果一段感情可以只剩下开头和结尾,中间所发生的一切都被擦去,或许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悬疑。没有人会质疑这头尾两端的真实性,也不会有人明白两个人是如何从开头走到结尾。
黎靖比我先找到房子,他搬走的那天,我们的旧房子还有十六天才到期。
“我们去旅行一次吧,说不定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他用力地关上那辆乳白色小面包车的后厢门,忽然转过头对我说这句话,额头上浮着细密的汗珠,在十二月的冷空气里像那天玻璃上的雨点一样反射着微光。
“好啊。去哪里?”我站在楼道的入口看着他,恍惚地想起我们搬进这幢楼的情景。
搬家师傅坐在驾驶位上摁喇叭,催黎靖上车出发。
“你进去吧。到了给你打电话。”他对我挥挥手,转身上了车。车窗后,我看到他还是在对我挥手,看嘴型似乎在说“赶快进去吧”。
两次跟黎靖在楼下分别,他都只说了这一句话。
黎靖搬走后的第二天,我开始休年假,我们定好机票飞往丽江。到丽江后找到长途客运站,跟同路的游客拼车到了束河。
在束河,即使没有方向感也不会迷路,只要跟着路边的溪流,决定是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
我们住的地方是一家小客栈二楼,木墙,木地板,木栏杆。床单颜色很鲜艳,开满了大朵各色的花。窗外的天蓝得有些失真,玉龙雪山的轮廓隐约映在远处纯蓝的背景上。
房间有些潮湿,但这几天却都没有下雨。我们每天睡到中午,起床后在古镇漫无目的地散步,晒太阳。老四方街、青龙桥、西山巷、红叶巷……每天都按照习惯的路线走一遍,常常迎面见到背着大筐的纳西族老婆婆,脚边不时跑过各色各样的狗。
“你觉不觉得这里时间过得很慢?每天都特别长。”我问黎靖。
他反问:“是不是感觉已经离开北京很久,像有半年一年那么久?”
这种没有重力的生活让我过得很恍惚,甚至有一些轻微的焦灼。我感觉此时此刻离开自己的生活太久太远,像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气球。
当你以为暂时逃离自己所在的世界会得到片刻的幸福,结果只是越来越惶恐,最终发现自己已经适应不了其他的世界。你不是无法享受失去压力的轻松,而是终于感受到没有重力,接触不到地面的恐慌。
夜晚的束河很安静。
回程前一天夜里,我们坐在客栈房间看电视。玻璃窗上隐约投影出远处的灯火,黑夜里寂静的空气有种潮湿的泥土味道。
我坐在床上边看电视边用干毛巾擦着刚刚洗过的头,黎靖调整姿势平躺下来,头枕在我的腿上。他没有说话,只是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撑开自己的眼睑,示意我帮他滴眼药水。
深绿色透明小瓶里的液体滴进了他的眼睛。他松开手指,眼睛因为药水的刺激不自觉地眨了眨,睫毛微微抖动,眼睑很快就恢复平静,安然盖住了深黑的瞳孔。
他闭着眼睛躺在那里,均匀的呼吸让我小腹处的睡衣一下一下有节奏地起了小褶。
“你要不要用?一会儿我帮你。”他依然闭着眼睛,轻声问我。
“不用,这几天眼睛都不觉得干。”我习惯性地伸手摸摸他的额头,用手指轻轻梳理他的短发。只要稍微低下头,就能听见他呼吸的声音。
“明天闹钟定到几点?”他问。
“九点吧。下午三点多的飞机,还是早点回丽江等着比较保险。”
“好,今天早点睡。”
“嗯。”
我们没了对话,静静地看电视。在过去的十一个月里,这样的夜晚重复过无数次。奇怪的是,当回忆起来时,我们都不记得曾经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内容,仿佛每次都只是共同对着一个发光的盒子各怀心事,记得安静温暖的感觉,却不记得看了些什么。唯一的例外,是搬家的第一天看到新闻报道的那场雨。
熄了灯的夜更加宁静。我们安静地躺在被子里,迷迷糊糊中似乎是同时翻过身抱着对方睡去。我在即将睡着的一瞬忽然惊醒过来,感觉到自己的脸正贴着黎靖熟睡的脸,眼泪无声地流下来,鼻腔和胸腔塞满酸痛的硬块。
我们如此熟悉彼此的身体,如此熟悉对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点习惯,我们甚至会不自觉地做同一个动作,任何一点互动都那么有默契。我们一直在彼此照顾,互相温暖,却从来没有接近过彼此的内心。
我们都觉得幸福。我们都觉得孤单。
从束河回来后,我的眼药水不见了。
我明明记得从客栈离开前曾将它收在化妆包里。每一样东西消失都会有它留下的轨迹,也许我只是迟钝,当时没有发现它的离开,事后无论如何回忆,都再也回忆不起来。
年假还有四天,我开始四处找房子。
那几天早上起来,我会依次打电话给搜索到的租房信息,如果没有约定当天看房子,就联系地产经纪寻找合适的地方。傍晚回家做简单的晚饭,到临睡前总会留出一点时间,慢慢收拾行李。
黎靖没有常给我打电话,在这种情况之下频繁联络多少有点尴尬。
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假期过完,该上班了。白天上班,傍晚看房,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我又恢复了以前一个人胡乱填饱肚子的日子。每天洗过澡躺在床上才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还来不及感觉到孤单,困意就席卷上来。
睡得很轻,偶尔失眠。但很庆幸的是,恢复独居后还没有过突如其来的悲伤或失落感。
我常常想念黎靖。做饭时以为他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关灯时以为他正躺在身边的枕头上,将钥匙插进锁孔时甚至觉得打开门后还能在鞋柜上看到他的拖鞋……
可常常想念这一切,却并没有让我难过。我知道记忆里这些片段是完完整整属于我,谈不上得到,也永远不会失去。
时至今日,我更加怀疑爱的本来面貌,它究竟是否与我们的想象有太大的差别。
我找到新住处时,离旧房子到期只有两天。
交了定金,签了合同,搭上回家的地铁已经九点半。手机在这个时候响起来,是黎靖的短信:“什么时候搬家?我来帮你。”
我输入了很多次,总是说到一半又删除。最后回复他:“我今天刚刚搬完,谢谢。”
很快再次收到了回复,他约我明晚一起吃饭。
回到家,我开始彻底整理衣柜和储物柜,将需要搬走的行李打包。我从阳台上收回晾干的衣服,坐在沙发上一件一件叠整齐。在一件旅行时穿过的针织薄外套口袋里,我摸到一团模糊的纸团,早已经被洗衣机搅得面目全非,只能隐约看到一排条码。
——那是两张登机牌。
在飞机上,黎靖把已经在检票时撕去了一截的登机牌交给我,说:“我们留个纪念。”
于是,我把我们唯一一次一起旅行的回程登机牌装进了口袋。
它们被洗成了一团模糊。
黎靖跟我约在第一次同事聚会的餐厅。
“搬到哪里了?”他刚坐下就问。
“离公司不远,坐车半个小时吧。”我略微低头,看到对面的他袖口有条细长而平整的纹路,一直从肘部处延伸到袖扣底下。只是轻轻动了动,那条纹路瞬间就不见了。
他把菜单递过来:“看看想吃什么。”
“都行,你点吧。我就来过这家一次。”
“我也是。”他笑了笑,“你挑吧。”
那顿饭吃得像平时一样平淡,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不痛不痒,不紧不慢。吃过饭,走出餐厅他到路边伸手拦车。
路灯下他侧脸的轮廓清晰又有点遥远。
“别拦车了,这么晚我坐地铁回去比较安全。”其实,我只是不想看见他再一次替我打开车门,站在小区门口对我挥手说“进去吧”。
“我送你到楼下。”他不明所以,坚持要送我回去。
“不用这么麻烦了,还是坐地铁吧。”
我不想再隔着玻璃看他的脸,看到他熟悉的嘴型,对我说“赶快进去吧”。那天朦胧的暮色不动声色地笼罩下来,他的声音终于渐渐消失在引擎声里。那一刻,离别平静得像不曾存在过。
他送我进站,我们乘坐不同方向的地铁。长长的自动扶梯一直缓慢地往下滑,他站在我身后,声音被电梯滑行的轻微噪音干扰得有些失真:“你恨我吗?”
“什么?”我回过头。
“你恨我吗?”他清晰地重复。
自动扶梯已经到底,我们并排走在空荡荡的通道里。
我低头走路,没有回答。
他问:“如果我当时愿意跟你结婚,你还会离开我吗?”
我转过身看着他,他的眼神还是那么平静,就像不动声色地跟我告别一样。爱有习惯,也有本能。我只是在那一刻发现了我们之间感情的缺陷:愿意互相照顾,彼此支持,却还犹豫不决对方是不是跟自己过完一辈子的伴侣。爱情在缺乏安全感的城市里犹如一场巨大的悬疑。
他的声音平缓而轻:“给我个答案,你恨我吗?”
我摇摇头,闭上眼睛。风从通道穿过,灌进地铁站台。
我在房子到期的最后一天搬家。除了大行李箱和编织袋之外,整理出六个纸箱,装满了我在北京四年的生活和记忆。我曾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努力回忆跟黎靖一起生活的日子,却仿佛什么情节都记不起来,像旧房子里那台电视机一样,还记得那种温暖幸福的感觉,却忘记了电视屏幕上曾有过什么样的画面。除了刚刚搬进来那一天,他向我描述量雨器的做法。
他说,谢珣,今年我一定会带你去旅行。
我们曾经以为那就是爱的全貌。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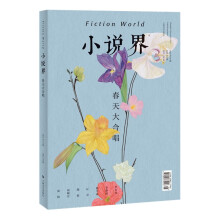

——读者 夏雨
一直很喜欢浅白色,淡淡的优雅、淡淡的别致、淡淡的幸福… …她的每一本书我都想收藏,这本书很值得期待。
——读者 SUNSET
听着广播里的音乐,洗完脸没来得及换下昨晚因睡着被压的皱巴巴的衣服,我也如果《MOMENT》里面的某位女主角一样,向青春的转角飞奔而去,等待我的下一站路口,我也不知道自己会遇见谁。
——读者 拓拓影子
有量度、刻度、重量、温度… …原来爱情可以这样计算,回忆的力量原来这样大,蝴蝶效应一般让我们记忆的太平洋也刮起了台风。
——读者 艾莫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