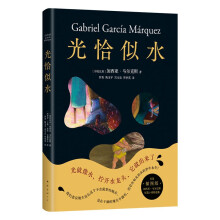于是,我和张藏藏约好,叫他带我去了一次。毕竟,他离我的家就三百米,我们是一个社区的邻居。我第一次去的那天,果然人很多。看电梯的女孩子一看我们,问都不问我们要到哪里,就直接按了6楼,于是,我们直接奔6楼而去了。到了607门前,张藏藏按了门铃。立刻,有一个人从里面把门打开了,是一个中年男人。看来,这个男人就是主人王可了,我想。我看他大约有四十多岁的样子,长着一张满月般的脸,眼睛很大,头上有些微微谢顶,嘴唇很厚,很温和慈善的样子,看上去还有些佛相。
“这是我的朋友,《北京时报》的文化记者梁大山。”张藏藏这么介绍我和王可认识了。王可对我微笑,“欢迎,欢迎!”在进门的地方,我们换了拖鞋,我发现,他家门口摆放的拖鞋非常多,各色拖鞋都有,至少有五六十双,显然是给很多客人准备的。
进了客厅,我发现,他家的客厅很大很空旷。在沙发上、餐桌旁已经有了几个人,或者聊天,或者在那里喝酒说话。于是,很快,我就适应环境了,因为,来了很多人之后,我发现我还知道一些人,他们大都是文化圈的人,作曲家、作家、学者、出版社的编辑、演员、导演,我还认识几个,甚至,还来了一个胖大的西藏喇嘛。于是很快,我就不拘谨了。这些客人是一个个地来的,一般都带那么一两个,男男女女都有,干什么的都有,场面很快就热闹起来了。
那天,络绎不绝的客人最后分成了三拨人,其中的一拨诗人兼书商,在客厅对着的一间屋子里玩砸金花,带彩的,输赢在几千块钱的样子,这几个家伙过去写诗,现在都成了书商,喜欢这个游戏。还有一拨人,都是喜欢书法的,有一个过去当了很多年和尚的书法家,还俗了,在那个屋子里,用一根像人的胳膊那么粗的毛笔,在给大家表演他的奇特书法。整个四十平方米的屋子地板上,铺的都是巨大的宣纸。而大客厅里餐桌上最后剩下了八九个人,大都是旅居国外多年,回来的学者、作家和教授。那天,刚好有一个黄莺子小姐,是在美国纽约大学里学习了多年的歌剧,个子很高,完全是一副美国做派,她刚刚出演了一部在国内走红的歌剧《银河》,又在广州出演了一部由一个美国女性主义编剧弄的歌剧《阴道独白》,在广州演了几场,可来到了北京,本来准备演出的,但是“阴道独白”这个名字听上去很令人有些忌讳,所以海报都贴出去了,最后还是没有演出成功。
我们都在谈论这个引起了争议的歌剧,于是,大家最后叫黄莺子小姐给我们现场演唱一段。这部名字听上去非常扎眼和火爆的甚至让见识短浅的家伙会感到匪夷所思的歌剧,是很有名的。说实话,我知道阴道是女人身上一个十分活跃的器官,但是,这个器官难道能够说话?我倒要好好听听它(她?)要说什么了。
黃莺子很大方地站起来,她说:“那么,我来演唱一段关于阴毛那部分的歌剧选段吧。”她酝酿了一下情绪,就开始给我们演唱了。歌剧选段是英文的,听得出来,这段歌剧十分有激情。女人的阴毛在说话,在歌唱十歌唱女人自己的事情,她们的麻烦,她们的复杂,她们的神经质,她们和男人的对抗与猜忌,和解与背叛等等。我听出来了,阴毛在悲伤和激昂地唱和说,阴毛现在不是隐藏在阴阜上的那一小片耻毛,而是有嘴唇的东西;这个嘴唇,正是被它所覆盖的那个要独白的生殖器官。啊,女人们!你们现在浑身的器官,都可以用来对着男人歌唱和说话丁!我陶醉了。
那天,三个房间里进行着三种活动:表演书法的那个书法家,已经用巨大无比的毛笔在十米长的宣纸上,写下了几个大字,甚至,有一张纸上只写了一个字:佛。然后,一个和尚就拿走了。围拢在书法家身边的有十多个人,在一旁也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是另外一种吃食。而在客厅这边,歌剧选段还在进行,阴毛部分的演唱竟然这么长,这么美好。客厅巨大,回响袅袅。但是美好的夜晚,美好的歌剧不停地被对面小房间的开门声所打断,门开了,我看见四个男人,诗人们和出版商,还有出版社的老总们,在那里吆五喝六,每个人身边都堆了一堆人民币百元大钞,红色的毛老头。在听歌剧的归国哲学博士梁造十分生气:“把那个洗手间的门关上!”于是,打牌的那个房间门重新又关上了。可是,里面的人总要出出进进,于是,“洗手间”的门就不断地被打开,然后被关上。里面的输赢已经见了分晓,兴高采烈和沮丧灰心的表情,被挂在不同的脸上,每个人跟前的人民币的高低已经不一样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