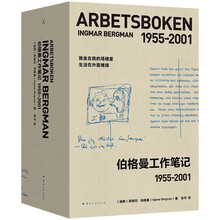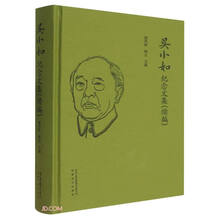倘若要说明这块方寸之地为什么属于小皮匠,大约就要涉及这近代城市的发展史了,具体地说来,且又是一些个别的人和事。最初时候,这片地方还是在城市的近郊,外国人在这里开了墓园,本地人称“外国坟山”。四周就有了一些鲜花店、蜡烛店,还有出售木雕和石刻的十字架、小天使、耶稣圣母像等等装饰墓地的用物。后来,墓园的边缘,那些连接田地的地方,被开辟出来埋葬中国人,墓园扩大了,周遭就有了中国殡葬习俗的店铺:香烛、纸扎、寿衣、锡箔、中国样式的棺椁。再后来,墓园越延越广,最深远处,其实已成荒冢。终于有一天,工部局征下地皮,准备建住宅区。第一要务清理墓地,也就是本地人说的“坟山”。先在报纸上登了七天启事,让中国人来迁坟,无人认领的墓便拾骨平地,一总焚烧,只留下外国人的墓地,用围墙圈起来。这样,周遭的殡葬业便不驱自散了。等这片地方建起几条弄堂和一排洋房,初具街区规模,就又有一些当年的旧业主回来,不过都转了行。有的摆水果摊,有的是馄饨挑,还有的做了看弄堂的人。其中有一个浦东人,原来是卖锡箔的,现在骑了脚踏车,车后面坐一个蒲包,包里面是河鲜鱼虾,挨家挨户兜售。渐渐与住户相熟,还和一个山东籍的巡捕交了朋友,就在一条弄堂口搭出偏厦,卖虾肉馄饨,将原先的柴爿馄饨挑挤走了。浦东人的女人也从乡下上来,镇日坐在弄堂口挤虾仁。后来生意做大了,巡捕又到别处为他找了地方开店。这偏厦,其实只够放一个煤炉坐汤锅的,巡捕又让给一个铜匠做营生。后来,巡捕走了,铜匠自作主张把地方让给他的同乡人,一个盐城乡下的皮匠。自此,这块地方就归了皮匠的行业以及家族。<br> 在城里,所谓皮匠其实就是鞋匠。城市里又不像农村,有牲口的鞍具络口什么的,除去脚上一双鞋还有什么皮具?这个皮匠将手艺和地盘传给了儿子,自己回乡下度晚年了。然后,儿子也老了,从小皮匠变成老皮匠。这个街区呢,随着城市的扩展。早已从边缘走向中心,但是,依然以居住为主,与闹市只相距一条马路。中间,皮匠也挪过几回地方。弄堂要卫生整顿,就让弄口的营生撤离,去什么地方?铜匠去了小菜场,补丝袜的女人回家里去,老虎灶关掉一个,那一家生煎包子铺归进区饮食公司,重新挂牌为合作食堂。皮匠摊收拾收拾,挪到马路对面,一排街心花园前。所谓街心花园只不过是一条两米宽的绿化带,沿墙十数米,墙里面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总是女生多,女生脚上的鞋是需要经常修理的,纽襻断折,后跟磨损,帮和底脱胶。皮匠摊跟前的小马扎上,常常坐着一个女孩子,脱了鞋的脚踩在另一只脚的脚背上,等待皮匠做完她的活计,这情景看起来挺温馨的。过了一阵,却轮到整顿马路了,皮匠摊就又要被驱走。他收拾收拾,再回到原先的弄堂口。那弄堂口多少有些阴暗,可是比较安定一些,过街楼避风挡雨,有一面墙根,可以堆放他的那些胶皮啊、鞋跟啊、钉子线绳,还有等着做的活计,或者做好等人来取的活计,也一并靠墙根。弄堂里的人,要么不来,要来就是一大堆,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单的棉的,但都不是急等,所以就放在他这里,过一两天再来取。也不要领取凭证,不见得能认识人,可鞋总归认识的,而且,鞋这样东西,也不怕别人错领的。安稳了一个时期,说不定又有哪一个部门来驱赶,皮匠总也没二话的,收拾收拾再搬,还是搬到马路对面。这一回可能不是在街心花园,而是一扇大门的门洞里。那幢公寓楼有着宽阔的门洞,但因为长年失修,门洞很破旧,木头门的油漆剥落了,墙壁和顶上的石灰也剥落了。皮匠摊设在台阶上退进去的地方,很妥帖,也很谐调的样子。要等到哪一天,大楼要大修了,皮匠就再搬出来。收拾收拾,回到弄堂口或者街心花园。总之,虽然是漂泊的,可总也漂泊不出这条街。倒未必是早年与山东巡捕的口头协议生效,恐怕没有人能够将历史回溯那么远,更不会有人认这本账。只是一个手艺人,他已经在这里做熟了,这里的人都是他的老主顾,他不能轻易放弃。这条街上的人,也习惯了他的活计,有时候他回乡下去几天,人们就将活计留着,等他回来做,并不会去找隔街的那个皮匠——顺便说一句,每条街都有每条街的皮匠。再说,他又不碍事的,各部门对他的驱赶其实也不认真,渐渐地,就形成事实。城管税务按月来收缴一些费用,皮匠摊就在弄口安顿下来了。现在,墙上敲了一排钉子,钉子底下是工具箱,一具铁皮柜。每天早上,工具箱横过来,与墙面形成一个直角,就成为一个小小的工作室。打开工具箱的锁,取出家什用物,一架缝鞋机放在地上,一些锤、钳、剪刀之类的小工具,一一挂在钉子上,还有一盘盘的胶胎,也挂在钉子上。工具箱的小格子里,放着胶水、钉子、纽襻、针线和鞋油。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