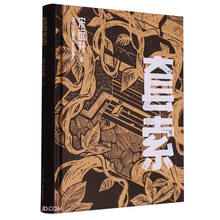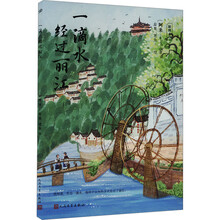拉下电门总闸,关掉自来水总开关、煤气总阀,插紧所有窗户的插销,锁了门,把一个热咕隆咚的家锁在身后,回老家过年的征程就从楼梯里开始了。<br> 楼梯里冷飕飕的,因为是早上,被驱逐在门外的隆冬的凉意一遇了人,就像一个长期流落街头的弃儿突然遇到亲人,冰冷的小手迅速抚擦过来,脸颊和鼻尖顿时冰凉一片。脸颊和鼻尖凉,浑身上下却一点都不凉,因为在此之前,我、丈夫、儿子、侄子,我们在楼道里已经上上下下搬运好几个来回了。我们不知道这栋楼里谁还是乡下人,谁还会和我们一样,要这么民工似的大包小裹地回老家过年,在这一趟又一趟的搬运中,我们没有碰到一个人。那清冷的感觉,好像年只属于我们,好像回家过年,只是我和丈夫、儿子我们三个人的事。<br> 年货把面包车的后备箱挤得满满,白酒、果酒、啤酒、饮料、火腿、各种熟食品,这些东西小镇上都有,可小镇上东西终归没有大城市质量可靠、上档次,你是城里人,总得上点档次。当然重要的是有专车,侄子开面包车专程从乡下来,你总不能让车空着。盖后备箱盖时,侄子一边呼呼喘着一边开玩笑说:“还有没有,要有还能装下。”<br> 侄子只小我三岁,大嫂生他时那一头黑糊糊湿漉漉的头发曾吓得我趴在母亲怀里号啕大哭。我们一起长大,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他因为酷爱机械修理,一直留在大哥开在小镇的修配厂里,最终也就成了关键时刻联系我和乡下家族的使者;我因为酷爱读书,一程程从乡村走出,如今成了媒体记者定居大连,最终也就成了每逢过年都需隆重对待的城里人。<br> 说隆重,是说侄子头天晚上就得赶到。从老家到大连不足三百里,并不算远,可因为我们返回的日子是年三十的前一天,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忙着贴对联挂宗谱,侄子必须在有阳光的正午赶回家里。提前上门等待出发,这等待的时光,不由得就有些隆重了。因为这个晚上,大哥会一遍遍打来电话,一会儿叮嘱侄子夜里早点睡,不能在路上打瞌睡,一会儿又叮嘱侄子再检一遍车,说上了高速发现隐患可就麻烦了,把侄子折腾得反而睡不着坐起来抽烟。点燃的烟头透过客厅的玻璃一星一星闪烁时,我仿佛看到大哥正热盼盼等待的目光,仿佛看到远在三百里外整个一个家族都在热盼盼等待的目光。<br> 大哥大我二十多岁,他一直扮演父亲角色,父亲去世后更是如此。十年前的冬天,他承包的汽车修配厂经营红火,买了面包车,提车的当天晚上就打来电话,“贞子,这回好了,来家过年有专车了。”那坚决而自豪的口气,仿佛他买车就为了过年时专程接我。<br> 为了这隆重的专车,我和丈夫大庆一迈进腊月就开始了隆重的置办,给母亲、大嫂、公公、婆婆买衣服,为娘家和婆家办年货,为大哥、二哥、三哥、公公、大姑姐夫买拜年酒。我们先是列个单子,写上要买物品的名字,算好要买物品的数量,定好要买物品的价格。娘家和婆家同在一个乡镇,办年货一式两份,列单子并不难,难就难在衣服和拜年酒上。大嫂的腰围一年一变,去年还是二尺九今年就变成了三尺一,公公的喜好很难把握,本来还说喜欢灰色,可你买了灰色他又说太旧,常常要提前打好几个电话。自从婚后第一年拜年,每家四瓶白酒两瓶果酒就成了铁定的规矩,每每想到改革,最终又因为种种不可言说的原因恢复照旧。按着记忆中的亲戚依次写来,往往写着写着就乱了套,因为亲戚有远有近,同是六瓶酒,价格档次总不能一样。调整、更改,毁了几次才写好单子,终于捏在手里,雄赳赳涌入闹哄哄的人流,可临了才发现,一切全不管用。因为你写的价格和货架上的价格大不一样,去年还是四十六块钱一瓶的老牌子酒,今年一下子就长到了七十六,巨大的价差映在眼前,握在手里的单子一下子就被汗洇湿了,要是此时再有人把你挤来搡去,不是踩了脚尖就是撞了肩膀,你的心突然就烦了,你不但心烦了,还忍不住一遍遍发问,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br> 年,实在不是个什么东西,对于我们这些在外的人而言,它不过是一张网的纲绳,纲举目张,它轻轻一拽,一张巨大的亲情之网立即就浮出水面。这张网其实从来都没消失过,它们潜在日子深处,藏在神经最敏感的区域,一有风吹草动,哪怕一个电话,都会让你惊慌失措。如果有谁身体不适怀疑得了重病,进城检查住到家里,你更是乱了方寸。只是很多时候,你努力忽视它忘掉它,你有太多属于自己的事情,职称晋级,孩子升学,房子搬迁,或者,你因为有太多属于自己的事情,不知不觉就忽视了它忘掉了它。可只要进了腊月,这张网就网进了大鱼似的,立即活跃起来鼓涨起来,一根根网绳在神经里绷紧抻直时,你不知不觉就成了撑网人。你成了撑网人,收获的却不是鱼,你没有鱼收获,自己却变成一条鱼被年收获,因为你必须为年准备巨大的开支。<br> 说到底,真正的纲绳不是年,而是身后的根系,是奶奶父亲母亲以及由他们延伸出来的血脉。你是血脉上的一个支流,回乡祭祖拜亲,不过是你的本分,可是这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本分之事,每做起来,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烦乱和苦恼,都觉得自己活得太累太委屈。你烦乱,是说你奋斗挣扎了二十多年,双鬓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却也没有把自己变成富翁,还要为几瓶酒钱算计;你委屈,是说你奋斗挣扎了二十多年,都由一个乡下人变成城里人了,餐桌上都有了蔬菜沙拉这简单的西餐了,最终还要为这繁琐的乡俗礼节费心劳神。<br> 侄子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感受,他一上了车就打开音响,播放新版邓丽君的歌曲,《欢欢喜喜过大年》。侄子当然是欢喜的,他一年到头起早贪黑从来捞不着休息,只有过年才可以喝酒打牌睡大觉。实际上,只要坐上侄子的专车,我也一点点有了欢喜的心情,这似乎和歌曲无关,而和车的速度有关。只要接了我们,侄子对这个城市就了无牵挂,出了小区直奔立交桥,密密麻麻的楼房在桥下倾斜时,你觉得有什么东西被你抛弃了,你觉得你对这个城市也了无牵挂了。<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