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这年头,谁不相信谣言才是傻瓜。很多真实的故事,都从谣言开篇。谣言总是不幸应验,这很让梅次地区的百姓长见识。谣言只不过多了几分演义色彩,或是艺术成分,大体上不会太离谱的。梅次这个地方,只要算个人物,多半会成为某个谣言的主人公。不然就不正常了。
朱怀镜自然是个人物,只不过他刚刚到梅次赴任地委副书记,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住房尚未安排妥当,朱怀镜暂住梅园宾馆五号楼。这是栋两层的贵宾楼,坐落在宾馆东南角的小山丘上。碧瓦飞檐,疑为仙苑。楼前叠石成山,凿土为池,树影扶疏。站在小山下面,只能望其隐约。小楼总共只有16个大套间,平时不怎么住人,专门用来接待上级首长的。朱怀镜住二楼顶头那套,安静些。套间的卧室和客厅都很宽大,有两个卫生间。梅次管这叫总统套房,就像这南方地区将稍稍开阔的田垄叫做平原。恰好是四月天,池边的几棵桃花开得正欢。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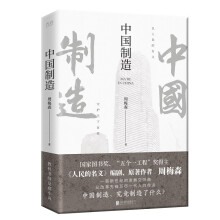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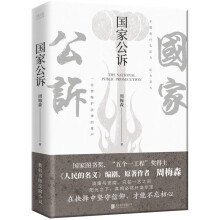


——《南方都市报》
以他(王跃文)秉直又清高的本性,不像是能混迹官场17年的公务员;但是,以他把枯燥无味的领导发言都能妙笔生花显出才华横溢的本事,又确实是当年机关里不可替代的笔杆子。1999年,36岁的王跃文以《国画》一举成名。这部描写官场风云的小说,把王跃文推上风头浪尖,一时间洛阳纸贵,连盗版书都不可一世地横扫全国。对于自己有着清醒认识与深刻反思的作家,是值得敬重与期待的。“我思故我在。文学应该是人类思考生活的重要方式。”王跃文说,他希望有一天静下心来,把自己的文字从头到尾再梳理一遍,多少年后回望时,能够感到欣慰,还能得到读者的承认。他说:“真正好的作家,小说要贴着地面写,要让读者回到现场。”
——《工人日报》
任何社会都应该有一点批判羊城晚报:隔了差不多十年,当年写《国画》、《梅次的故事》,今年出版了《苍黄》,其间心态有什么样的变化?王跃文:应该说是有一些变化,因为我创作《国画》的时候也就三十五六岁,在官场里面看到了很多的人和事,那个时候可能比较“愤青”一些,有人评价《国画》是一部“孤愤之作”,我承认有自己对现实的一些观察思考;那么到了《梅次故事》,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到了写《苍黄》的时候,我是看到生活中更多的丑陋,但是没有改变我对生活的真正看法,批判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羊城晚报:谈谈你的批判立场?王跃文: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坚持一种批判立场,我认为都是一种很可贵的态度,从来没有一种最理想的社会,没有过,因此在任何国度任何社会任何民族里面,应该有一点批判,这是必须的。如果一个社会所有的人都不敬畏,认为到了太平盛世的话,那可能很危险了。羊城晚报:你的官场小说跟现实生活相比有什么不同?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更戏剧化?王跃文:如果靠某一部小说或者其他文学作品,去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某一方面的现实生活,这是做不到的,也没有,文学也没有这个义务。如果说真实性,我觉得有时候文学体现出来的真实可能比现实生活更真实,更典型化;如果说戏剧化,有时候官场中真实发生的事情,更加戏剧化,比如生活当中有一些真实的事情照搬到小说中来,读者可能还觉得你这个是假的。我在《苍黄》里写到过,当地的政府将上访的人送到精神病院去,许多人就说,这是真的吗?怎么那么黑啊?我上次就看到山东什么地方的报道,确实有这样的事。我今天坐飞机来的时候,又看到一则报道,河南某地一个农民告乡政府,就被当作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去关了六年半,但是后来经过检查,一切正常,根本不是精神病。
——《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