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上顶着触角,在关节处弯折着。一双与身体尺寸不协调的大眼睛,大小有自己小指指甲的一半。她把小指伸过去,它咬上来却并不觉得痛。她发现了一件事:这种蚂蚁不会咬人。她只想看看蚂蚁王国的内部,剪下一块偷偷观察一番。
今天早晨穿过树林的阳光似乎多了些尘土,微粒夹着潮气,在她身后的树林里拢成阴霾,她的这棵树的叶子和枝条就更衬得鲜明。没有一片树叶在摇晃,现在所有一切都纹丝不动。鸟儿们从一棵树唱到另一棵树,鸽子在唱丧歌,麻雀叽叽喳喳,啄木鸟一路叩叩打打上了树,停下来看了看她的小舟,又飞快地在她揭开的蚂蚁窝上忙碌开了。一个礼拜以来它已经来拜访过好几次了,开始把她当作这棵树的一部分。
这个平台是个正方形,六英尺见方,是用厚木板扎成的,仅能容得下她和一些补给品,还有一把帝王般的座椅,是雅克用弯柳树枝做的。这把椅子让她能够放松臀部和双腿,一年来她的臀部和双腿萎缩不少。她现在似乎完全失去了行走能力,雅克花费大把时间和金钱给她制造运输工具,仿佛她是一只体型硕大的幼鸟,不停地从一个巢穴转去另一个巢穴。在上面她根本用不着出声,而她却出声了。第一天上去她就开始跟树世界的居民倾诉心声。自她大声说话那次过了好几天,雅克依然为他自认为的进步而眉开眼笑。他相信自己救了她两次。
啄木鸟背上生着黑白相间的条纹,大小跟知更鸟差不多。她又在画它了,这礼拜的第十次,努力抓住它在运动中的型体。它要能停下来就好了。昨天又有一只跟它一起来了,她开始明白过来更花哨的那只肯定是雄的——红冠红颈——雌的则只有红颈。由于处在特殊的角度,她可以看到两只啄木鸟的腹部都有一块玫瑰色的斑纹。雄啄木鸟在啄树吃蚂蚁的间歇,会反复发出颤鸣或者嚓嗑——嚓嗑——嚓嗑的声音。她记录下来,想再画一次。
“把蚂蚁吃光吧。”她轻声说。
她把食物篮子打开,拿出一罐冷的甜茶和一块饼干。安妮不肯多吃一口蒂丽烧的饭,这让蒂丽羞愧难当。带着负罪感,她越发痛苦和懊悔,但是还有别的秘密在燎灼着她的面庞和双手,又在眼睛周围画上了黑眼圈。安妮发现一旦摆脱人们的视线,蒂丽就立刻失去了理智,似乎有什么奇异的魔法在作祟。某种巫术。从她所栖息的地方望出去,雅克买卖各色物品,提供各色服务。一个礼拜里每天都有特别的比赛,使雅克更快地累积财富。今天斗鸡,明天赛马,接着又是拳击、摔跤、猎鸟、耍刀,等等。晚上他就睡在她身边,把他的王国细细梳理一遍,让她知道各部分分别贡献了什么,让她知道他为她积累了多少财富。“你看我爱你有多深,亲爱的?”见她默不应声,他就接着说,“房子盖好以后你就会同我讲话吗?”
大家不理解他的意图,尤其是今天早上。“我以为你要我们铺柏木地板呢。”斯卡格斯说。他搔一搔花白的胡子,抬头看看雅克建在这座小山上的豪宅。去年秋天屋子的外部结构已经竣工了,但是内部装修迟迟还没有开始。窗棂又没有装玻璃,鸟儿和其他动物已经做了窝。
裴澈尔,威尔拾起一把用来开槽的犁刨。“木板切割好了,就等开槽了。再在外面放着会变形翘起来的。不该无谓浪费那么好的木材。”他朝那高高堆起等待拖进房子里的木板点点头。
雅克一扬眉毛:“先做圆桶。用橡木。”斯卡格斯刚要开口,就被雅克抬起的手堵住了。“我知道橡木是用来做门的,但是现在不再是了。”他看看头顶赫然耸立在山上的房子,“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钱,不单单建造一所房子而已。”圆桶是用来装啤酒的,雅克要自己生产啤酒。一个德国酿酒师傅昨天才到,而且并不打算要留下来,到夜半时分他把钱全部输给了雅克,又输掉一包衣服。玩牌的时候就连马甲上的银钮子也输掉了。雅克把他囚禁起来——“你教我的伙计酿造和在德国一样好的啤酒,我就放你走。”
斯卡格斯叹了口气,朝柏木板看了最后一眼,把目光转向山下,看看树上的安妮,她似乎漂浮在那棵老橡树的繁枝茂叶之中。他摇摇头:“可惜了好木料。”
雅克伸开两臂:“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就一定要得到。如果我选择把客栈送人,住在树林里,就得这么办!”
“需要多少圆桶?”威尔问道。
雅克的手下现在对他的恐惧多过尊敬,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尽管大河上下客栈为数稀少,但他的客栈却开始臭名远扬。是她的错,她知道,因为她没有尽到做妻子和助手的责任,没能让他专心致志为这个家庭谋幸福,而幸福这个词让她痛苦。
斯卡格斯和威尔开始做圆桶,雅克坐在她那棵树下的长凳上望着大河。就在大家刚才站着的地方她看到有什么东西在发光,她又一次举起望远镜。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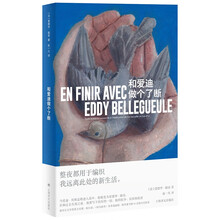
——《美国今日》
迷人的家族故事,丰富的历史细节,充满危险的情节,爱与背叛,华丽的外表,令读者流连忘返
——《出版人周刊》
约尼斯·艾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难以忘怀的歪斜世界,其中充满了秘密和令人心碎的爱情,甚至还有深埋着的宝藏。
——邝丽莎,《雪花秘扇》
作者最棒的南方哥特传统中满是激情、背叛与不幸,这些催眠的故事充斥着值得纪念的人物和描绘清晰的边境生活。
——Book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