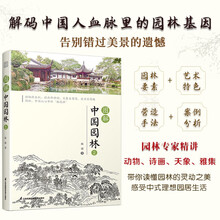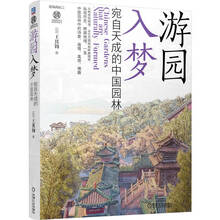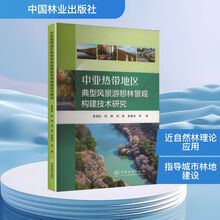诗意的园林为人类再造乐园
生物的基本需求是呼吸、饮食、繁殖自身。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大部分物种来说,这些基本的需求之外还有栖息的需求,即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某处占据一块地方的需求。鸟类靠声音宣布地盘,它们的鸣叫声标记其属地的边界;狼利用气味作为界标。人类自出现在这个星球上起就一直在为界定、捍卫和扩张领土而战,甚至献出生命。文字、房屋、纪念碑都可用来歌颂领土,同时又为其增光添彩;在某些特殊之地和某些特殊时期,园林的出现使其趋于完美。园林的溪流、树木、花草以及山石,用以欣赏或是纪念;园中的秩序实际上是我们自身在地球表面的延续。本书就是为那些真正喜爱园林风景的旅行者、设计师、园艺师和普通大众而写的,这些园林风景很多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21世纪的某个时候,日本平安时代几近结束,一位不知名的日本宫廷贵族定下了园林艺术的规则和注意事项,并集录成书,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作庭记》。他的建议非常简单:开始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地与水的布局,研究过往大师的杰作,回想记忆中的美景,然后,在选定的地方让记忆说话,把最感动的东西融入自己的构建之中。为探索这些普遍规律,我们研究不同民族在不同时代、不同气候和不同地方修建的园林杰作;学习其设计手法,记住它们的形象、气味和声音;收集、再造并转换设计材料,按照我们有意义的秩序排列;缩小规模,最终融入我们现有的场地之中(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多,这样的地块变得越来越小了)。
一开始我们会考查使一个地方有望成为园林的那些条件:水与地的格局、现有的植物和进一步拓植的可能性、与周边人类居所的相互关系,还有建筑的形式、太阳朝向和风及星星的方向、当地的白昼与季节的周期,以及与已经消亡的时代及遥远的地方之间通过记忆形成的联系。不管我们觉得多么壮丽动人,大自然的某些地方却还不是园林本身;只有通过我们的行动加以塑造并与我们的梦想融为一体,它们才能够成为园林。因此,我们会继续考虑塑造园林的那些行动:为大地塑性,划定界限,通过墙体、屋顶、道路和纪念碑等与空间产生联系。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几十处人一生都梦想去旅行和朝拜的世界顶级风景和园林,不仅用来欣赏,同时从中挖掘园林设计的思路。这是本书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细心挑选每一处风景地(基本都配有大幅轴测投影图),带领大家游览,为大家讲解其历史,考查对园林知识来说最重要的模式和概念。在不同的文化、时代和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可能出现不同的园林,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我们的例子无所不包,从古罗马到现代英国,从乾隆的圆明园到沃尔特?迪斯尼的魔幻王国,从喜马拉雅高山上的僧院到博特尼湾海湾的囚禁地。
最后,我们将检阅往昔伟大的园林传统在北美大地的移植和适应,想了解这些传统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作为读者参加旁听,发掘其中对于现代园林设计的暗示和启发;看看过去那些出色的园林格局和思想如何被挪用、再解读,最终演化为我们自己的园林。如艾略特在《圣木》中所言:“不成熟的诗人会模仿,成熟的诗人会偷窃;较差的诗人把别人的东西拿来毁掉,而优秀的诗人会使其变得更好,至少会使其不尽相同。”
龙安寺
艺术家最基本的冲动之一是简化、清除,用越来越少的东西表示越来越多的意义。日本枯山水的水通过沙子来暗示其存在,雄伟的山峦不过用几块小石头来表达,这或许是园林的终极理想——思维景观。在这样的园林当中,如15世纪的一位禅宗僧人所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艺术,致使三千里江山尽收于方寸之中”。他有可能是京都附近的一座寺院,也就是著名的龙安寺的设计者。
龙安寺园有网球场大小,铺着细心耙好的闪光石英,西面和南面立着低矮的围墙,墙外是浓密的森林反射出青葱的微光。南面及东面的大部分都是带游廊的平台,供游客观赏沙园。
沙地上摆放着15块石头,分五组排列。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最多只能看见14块。石头在和谐惬意的氛围中激起游人的好奇心,纷纷用各种形象来解释这一组合。有说是虎妈妈带着小老虎渡溪;有的说像海景画,以沙为海,以石为岛。还有人将其解释为宇宙中固定点的图形,还有更有禅宗的解释,说这些就是石头。伊藤贞司在《日本园林》一书中称之为“园林的理想,它是完美园林的生动蓝图”。
根据我们的图形来琢磨着15块石头与实地观察是两码事,但是,哪怕在这样一些轴测图里,它们也能散发迷人的气息。它们是那样的完美,各组石头内部和各组石头之间的平衡处理得如此巧妙,在全神贯注的观察者心中激起了内敛的平静。但究竟为什么如此,我们不想不懂装懂。没有哪一种宇宙哲学的解释能够真正说服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但是,毫无疑问,带有感染力的力量就摆在那里。
日本园林界另一位权威早川方夫指出,我们今天如此器重的石头实际上在龙安寺建成200年之后才被人提及。他认为,在此之前这个园林的主要景观是一簇樱树,其中一棵还是著名的独裁者丰臣秀吉造访时亲手栽种的。他栽下的那棵树的残迹今天仍然可以在角落看到:看来经过部分擦除,场景的隐喻变得更加精致,默默无声却趋于纯粹。
龙安寺以微缩取胜,将宇宙浓缩在几英尺的天地之中,简化、削减、压缩、删节那些对中心思想没有直接作用的东西(当然,毫无疑问,龙安寺的确有其中心思想,尽管园中景色一直带着我们围着它打转)。20世纪末期,我们大多数人依然将沿着微缩景观的道路走下去,将整个世界浓缩到合适的场所之中。龙安寺的案例表明,景观经过大幅缩减之后,不仅仅反映浓缩的现实,而且还能够形成更加纯粹和自由的新视野,并且跟宇宙同样宏大(艺术家一直都清楚这一道理)。
“万能布朗”的公园
沙漠民族想象中的天堂就是凉爽的绿洲,里面有潺潺流水和果实累累的树林;猎人则期待布满猎物的森林。《圣歌》反映农牧民族的渴望:绿色的田野、安静的水面,还有能够保护他们的牧人。18世纪下半叶,风景园林家万能的布朗在英国的乡间多次将这一田园理想变成现实。
布朗为其贵族赞助人建造的那些园林的基本要素,不过是随处可见的风景:起伏的山坡,山坡上的草地和树丛,牛羊和鹿漫步其间;平静的水面、薄雾以及云朵。他以这些元素的现有形式为建园起点。也就是说,从这些场地的“潜质”出发,然后加以“改进”,使其更接近他的自然美的概念——像辉格党人一样,他对通过渐进的改造和调整逐渐趋于完美充满自信。布朗是位讲求实际的人,并不太在乎理论分析,不过两位和他同时代的人所提出的“美”的定义却对他的设计意图做了很好的阐释。哲学家埃德蒙德?柏克在《崇高与美丽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一文中提到,美存在于小巧、平滑、规则、渐变、精妙与和谐之中。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提醒读者留意“坐在轻便马车上快速地驶过一片平整的草地时产生的那种感觉,那种渐次上升和下滑的感觉。这一点”,他说,“比别的任何东西更能说明什么是美”。画家威廉?赫加斯在《美的分析》中倡导使用起伏的“美之线条”。这是一条优雅的曲线,不是洛可可紧绷绷的两维曲线的扭动,而是一根平缓、放松的三维蛇形线条。霍加斯在人体中看到了这样美丽的线条,也在齐本德尔家具中看到了这种美;布朗作品中也随处可见。
典型的布朗风景是一个开阔的公园,里面有宽敞的乡间别墅。房子周围是平整的草坪,有时候,草坪还会爬到墙上。这样的初步“改善”通常伴随着对邻近原有旧园林(通常是规则式园林)的破坏。评论家并不总是支持这一做法。佩恩骑士后来抱怨“改进者的破坏之手”让房子
被修剪草坪包围,
在无限起伏的空地上苟延残喘
为防草坪被园林内栖居的牛羊毁坏,同时又保持前景和中景视觉上的连续性,布朗经常会用到低矮围墙。这一手法成了典型的布朗,以至于后来的评论者都错误地认为这种低矮围墙法是布朗发明的。
一般来说,草坪会顺势而下,延伸到宽阔河流或湖泊的岸边。这样一来,从房子望向园林,或者从园林回头向房子看去,水成为处于横亘其中的元素。水体的形成取决于现存的地形和排水条件,不过水体特征却源自布朗的园林美之理想。
第一个理想是,水体与房子和周围风景之间应该形成体面的比例关系。一般来说,这意味着必须修建水坝。但是人工结构必须不留痕迹,水坝要伪装起来,人工河流要在远处自然地消失。利用山坡和植物可以掩盖两端,达到隐藏的效果;也可以用假的桥梁来掩盖堤坝。堤岸要有美之线条的曼妙曲折,同时与灌木和树丛保持一定距离。
以威尔特郡的波伍德为例,布朗在两条溪流的汇集处筑了一座大坝,形成Y形的水面。大坝掩蔽在带形的树木之后,从别墅看过来,这一排树木就成了水景的背景。堤坝形成林间飞瀑,只有环湖漫步的人才能够发现这个惊喜。背临树木,形成房子和草坪方向的景观焦点的是一座多利安神殿,它吸收夜晚的光线,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白色的倒影。
在苏塞克斯的佩特沃斯,布朗的湖泊则展现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潜质。在这里,水体被安排在缓坡草地浅浅的凹陷处。海岸基本上没有树木,因此,蛇形的线条在草地与水面相接之处清晰可见。视线通过周围起伏的山坡和精心布置的隆起以及带状树林来确定。因此,观者透过缝隙来观赏湖泊的片段:蓝天在湖面投下倒影,大雁的叫声在湖面上回荡。
越过前景草坪和中景水体,布朗还设计了起伏的草坡背景,其上点缀树木,似乎向着远方无尽伸展。为了塑造“缓缓上升和下降”的景观,他不能够像我们今天一样大兴土木(不过,他的确填平了一些沟壑)。相反,他巧妙地利用树木来修饰外轮廓:顶部栽树造成上升感,用植被填平深沟使其平整,并把风景当中不想为人所见的部分掩盖起来。现在我们在佩特沃斯仍然可以清晰地观察这一点:树木的图案覆盖地表,如同立体剪裁的衣服一样。
在树木的处理上,布朗遵循后来人们熟知的带状、团块和点状种植原则。带状种植的树木沿着园地外围轮廓线排成一条条曲线。团块种植十分紧密,大致呈环状,与周围的草地形成鲜明的对照。点状种植的树木散步在草坪和草地上,可以单独一株,也可以组成小的一丛。托马斯?洛夫?皮考克在他的小说《海德隆大厦》里拿布朗的种植开涮。小说主人公帕特里克?奥普里塞姆爵士(风景画品味的倡导者)毫不客气地奚落布朗的一位崇拜者:
平整、修剪、堆土、抛光、抹光、播种然后收割,你用的这些方法不仅破坏了自然妙不可言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光与影渐次的和谐也没放过。它们原本水乳交融,如同远处那块石头一样自然和谐。我从来都没有看到你所说的改善之地,那不过是硕大的一块绿地,单薄得如同一张张绿色纸片;这里那里散落的几处圆土堆,如钢笔随意甩出的点点墨迹一样。哦,还有那几只动物,孤零零地被摆在各处,看上去像是迷途羔羊。我觉得这些跟整个豪恩斯洛没有一点契合之处,那里不过是长满灌木的强盗之地。
山上不仅有树,还有动物。在郎利特的佩特沃斯,以及几处保留至今的布朗园林中,我们仍然可以看见鹿和牛排成长队在林间穿行,羊在山坡上悠闲吃草。它们带给风景尺度感,观赏者一看便知树木的大小和整体景深。另外牛羊的啃食能够保持草地表面和树根部的平整,从而使得观赏视线与地面保持齐平。
公园的周界一般是由带状树林组成,其间点缀土堆显得自然。在波伍德和牛津附近的温波尔,能够清楚观察到此种手法的运用。在带状林合适之处会留出空隙,便于在园中观赏园外景色。如果树林看上去缺乏特色,可以通过一些建筑上的要素予以激活,比如波伍德的神殿以及桑德森?米勒在温波尔附近做的仿哥特废墟,以取得油画一般的效果。头顶之上是风景的尽头——云彩点缀的英国天空;那起伏不定的大块云团几乎就是地面风景的翻版,同时将大片阴影播撒在山坡上。
布朗建造了数十处伟大的园林,但是,到目前为止最宏大的一处是牛津郡的布伦海姆,前后对比图能够很好地反映布朗改造的效果。
布朗发现在布伦海姆存在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协调,主要是约翰?马尔伯勒公爵的宫殿的巨石与格林姆河的涓涓细流之间的比例问题。另外,宫殿正面有一条轴线跨过了小河,为了强调这一轴线还在河面上修建了一座巨大的石桥和跨河公路。布朗对格林姆河谷的排水系统做了些调整,修建了一座大坝;同时在宫殿的南边形成一处巨大的瀑布,并做了很好的伪装。这就在谷地的河床上形成了一个开阔的不规则湖面,带着心满意足的贵族气。不仅如此,桥拱下的水面得到提升,平静的水面反射出桥梁美丽的倒影。布朗还对湖另一侧的背景进行重组,把它变成了由土堆、带状树林和薄雾组成的远景,羊群在树下安静地吃草。
布朗理想的风景并不是龙安寺那般摄人心魄,也没有朴实到严苛。但是,把景物缩减为最基本要素,明确关系,剔除瑕疵和不完美处,两者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这与同时代的约书亚?雷诺兹在油画人物中根据传统的贵族气传统来修饰面部的瑕疵有异曲同工之妙。布朗的目的并非打造《阿恩海姆的乐园》里不可思议的完美以及不切实际的关爱和兴趣。他不过简单地消除大自然偶尔出现的瑕疵,让自然内在之美自行呈现。龙安寺砂石平面的石头蕴含着山水禅意,同样,布朗在英国绿草丛生的起伏地面和宜人的陆上风景里种植的大批树木也向我们展示了其本质——即18世纪辉格党人或是柏克对风景的定义。
巴厘
在我们这个星球之上,几乎没有几处秩序井然的封闭世界,为独特习俗和文化的形成提供地理背景。但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就有这种独一性,并且形成了带有强烈自身特质的印度教本土文化。
今天,可以乘坐大型喷气客机到达现代化首都登巴萨。但是在过去,要从爪哇前往巴厘。从巨大、破旧且潮湿的港口城市泗水出发,这里即是布莱希特让冷酷的约翰尼歌唱民谣的地方:约翰尼在泗水的岸边,抽着水手的烟袋,抛弃了他的女人。从市立动物园(里面有可恶的蜥龙)坐公共汽车出发,沿海岸的咖啡园向东走到令人昏昏欲睡的巴奴万吉村。在这里,和当年入侵的爪哇王子一样,乘渡轮涉水而过到达巴厘的吉利马努克。公共汽车沿着巴厘岛南岸一路向东,最终到达登巴萨。
巴厘的西半部是令人失望的地方,只有一片小小的红树林沼泽地,里面生活着鳄鱼和有毒的蚊子。但是,一路向东就会发现,在酷热的赤道阳光照射下,地形在慢慢变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些很陡的火山山峰,这也是岛屿东西向的骨架。最东边的山峰,也是岛上最高的一座,是阿贡火山冒着烟的锥形山口,最高处超过一万英尺。向南是深不见底的沟壑,溪流从山上奔流而下,流向大海。山海之间的狭长地带被修剪成精致的台地,亮绿色的稻株夹杂其间。沟壑和没有种植的山坡覆盖着过于茂盛的黑色丛林。公路和小路在这片陆地有节奏的起伏之间蜿蜒逶迤。有些顺着东西向的轮廓走,另外一些与沟壑平行,形成蜘蛛网一般的平面。山与山之间,与稻田为伍的是一些小村庄。至关重要的集市和行政中心,比如塔巴南、登巴萨、吉安雅、克隆孔和阿姆拉普拉,都位于低处的山坡或是沿海平原上。南部崎岖的武吉半岛伸向大海,如同乘风破浪的船首。其余的海岸是椰子树和香蕉树装饰的慵懒沙滩。
这里是活火山带:火山口不时冒出一阵阵的浓烟,海滩由洁净的黑色火山灰构成,雕像刻在凝灰岩里;有一些祠庙尽管几乎都被火山灰和岩浆所覆盖,却依然在使用。这些东西让人想起地底隐藏的自然力量。火山既是创造者,也是毁灭者。它们形成了山冈和水源,肥沃的火山土滋养两边稻谷的生长。但是,它们有可能突然之间就将田野吞没,人类居住地会被寸草不生的灰尘和石头所覆盖。
这里也有安静的纯真之处,在阳光照射下散发出美丽的光芒。清晨从安静的稻田之间走过,薄雾从地面和山上升起,远山呈现温柔的蓝色。也有一些鬼魂出没的邪恶地方。在果阿牙也,龇牙咧嘴的巨眼怪兽在活动的岩石间挣扎,张开的下巴形成山洞的入口。库桑巴附近有一个蝙蝠洞祠(印尼人称之为Pura Goa Lawah),哪怕在明亮的下午也有一大群蝙蝠在这里呼啸盘旋;身上溅满蝙蝠粪的僧人和因患疥癣而脱毛的狗一动不动地坐着。在树丛和庙宇的庭院中,有时会遭到一队愤怒的猴子的伏击。山上有一个火山湖,湖里有一座岛。踏上岛屿,就会发现不友好的村民用平台上风干的尸体来表示欢迎。
如果在清晨进入巴厘村庄,经常会遇到孩子们赶着大群的鸭子到稻田里去放养。他们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后,在地上插上一根竹竿,竹竿下面放上一盒饲料。这个地方就是鸭子世界的中心,它们整天围在它周围,直到晚上一个孩子走到它跟前拔起竿子,再将它们赶回村庄。
阿贡火山的锥形山顶处在这个岛屿的中央,同样也是当地人生活的中心。云开雾散之时,从岛上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它,人们清楚地知道那是生活的来源、宇宙的轴线,也是神的住所。根据巴厘宗教的传统,围绕着火山,相对立的魔力在流动。掌管生育和生命的神(卡娅)从山顶之源顺势流入溪谷,而危险、灾病、死亡之神(克洛德)源于大海,并且逆流而上、兴风作浪。切断这个流向的是第二根轴线,由日升日落的方向来确定;日升对应卡娅,日落对应克洛德。白昼与黑夜、生长与腐烂、孕育与死亡的自然周期,即卡娅与克洛德的交互与对立。生命发生在以阿贡火山为中心的世界,周围是充满敌意的大海,由两种力量所统治。
高山、大海和太阳形成力场,就像磁极一样,里面的一切都是铁屑。高地和上游源头纯净且安全,不会受到腐烂和死亡的威胁。高坛之上摆放牺牲贡品,敬献给掌管生育和生命的天神。床头都朝阿贡火山,或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如果你希望在谈判中处于优势,就必须想办法站在上坡的一侧。相反,坟墓和十字路口都不干净,并且危机四伏;地上摆放的贡品都是献给阴曹地府的神灵的。
山冈和大海之间的大地进一步细分为下降的梯田。这些纵横交错的梯田由合作社(subak)共同开发和管理。一般来说,一个苏巴克占据一个山脊或山谷,在上头修建水坝,拦住一条从山上流向大海的溪流。从这里开始,水流被分开,流向各块梯田。每一块梯田四周都有泥做的土坎围合,土墙上留有缝隙,供水流通过,沿着卡娅—克洛德的轴线继续流动。这里,土、水和太阳同心协力参与到稻谷生长、结实和腐烂的周期之中。
巴厘人的房子将人类生活的周期圈在泥墙(有时候是砖墙)之内。院墙围成庭院,一般只开一个门。门的朝向也有讲究,一定要对着吉利的方向。大部分的日常起居活动都在露天里进行,小小的亭子(一般是两侧开口)散布在庭院里用做仓储、休憩、避雨;庭院中还有遮荫的树木。不同用途的亭子的位置也由方位系统决定。向山坡的那个角落,离太阳升起的地方最近的,一定是祖祠的位置。
庙宇是神灵的住所(巴厘有很多这样的庙宇),因此这些庙宇的布局跟普通人的房子有很多相似之处。庙宇一般是由三个长方形庭院组成,跟梯田一样一个接一个从低到高排列,形成从污秽到神圣的朝圣之旅。庭院之间的大门都修成精美的高塔,上面装饰着雕塑;怒目圆睁、伸长舌头、露出毒牙的雕像是庭院的守护神。有一种类型的大门在开口处的上面竖起牌楼,还有一种类似印度寺庙的“裂门”,从上到下一分为二并且分开一定距离——这是对于穿透边界这一行为的充满力量的戏剧化展示。庭院之内,有亭台用于储物和表演,另外一些用于居住和供奉神灵的牌位。
庙祠的平面设计巧妙地与方位系统相呼应。从下往上,大门的位置都有稍稍的偏离,以防止阴间的魔力长驱直入。亭子和神的牌位安放也不对称:一般来说,亭子和神龛会在庭院的上山(巴厘南部一般是指北边)和日出的方位(东边)形成一个肘弯,最重要的部分(湿婆的莲座)放在庭院东北角。清真寺的建筑师必须想办法让寺院大门既朝着麦加,又对着大街。巴厘的寺庙也是如此,其平面必须经过调整,以使客人能够方便地从大街上进入庙宇,同时朝着阿贡火山的方向前进。
村庄是房舍和庙宇通过简单的循环系统构成的一个组合体,正如苏巴克土地由水系统连接的梯田构成一样。虽然并非所有村庄都在各个方面符合这一点,但是,巴厘岛上却有一个严格定义的传统布局:主轴线沿着山海之轴南北贯通,次轴线与日出——日落轴线相平行。轴线相交之处即是村庄的中心,也是市场的位置所在,通常以一棵巨大的老榕树为标志。村子里一般会修建三座庙宇:普拉普塞在主轴线上坡,专门祭祀主管创造力的天神;普拉德萨(或称普拉巴雷阿贡)位于中心附近,供开会和举行仪式使用。还有普拉达勒姆,位于下山处,靠近海洋一段,专门供奉死亡和腐烂的神灵。紧挨着它的是一个墓地。各家的大门朝向两条街道,有时候还朝向第二条由背街的胡同构成的后街。因此,街道、庙宇和中央的榕树构成方位系统的轴线、两极和中心;正如溪流、太阳的弧线、阿贡火山的垂直山体以及海洋更大尺度的排列一样。
村庄的街道是举行仪式的舞台。宗教节日到来之时(这样的日子无以数计),大家排着队,在加麦兰乐队的伴奏下,抬着牺牲贡品热热闹闹地行进;穿过装饰得五彩缤纷的街道到达庙宇。举行火葬之时,人们抬着色彩明亮、装饰精巧的花车走下山去。他们大声喊叫着,曲里拐弯地行路(这样死者危险的灵魂就与轴线擦肩而过,并失去方向感),赶到靠近普拉达勒姆的一个地点,并在那里燃起大火。
在巴厘南部,村庄与稻田都紧密地挤在有缓坡的平原上,头顶威严的山峰,下踩令人退避三舍的大海。巴厘人传统的宇宙观赋予这种垂直空间分割更深刻的意义。根据传统,巴厘是一块岩石,一只巨龟骑在这块岩石上游于大海,岩石之上是湿婆的住所。庙宇的湿婆神龛生动地展现了这一传统:下面是龟底座,上面是迎接湿婆降临的座椅。在房舍和庙宇里发现的亭子尽管外形各异,但都反映出这种模式:都有一个基座,将人们从地表的危险之中抬升起来,然后是人类的居住区;最后是屋顶,让人联想到高耸的阿贡火山。
在一些重要的庙宇中能看到一种特殊的亭子,叫做梅鲁。这名字将亭子同印度传统的核心的圣山梅鲁山联系起来。梅鲁亭是高耸的狭长多顶塔,有好几层屋顶,屋顶的数目代表亭子的重要性。在幽雅美丽的乌鲁达奴庙宇里,每一个梅鲁都立在坐落微小的围合岛的中央。这是阿贡火山的微型缩影,周围是微型的巴厘岛本身。
通过一个中心的方位轴线中的三个主题——围合的边界、门神看护的大门,以及处在阴间与天堂之间的人类居所,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覆盖全岛的庞大的庙宇系统。从海滨开始,这里被看做人类住所与外面的危险世界的一条界线,是进行净化仪式和与阴间力量和解的地方。塞朗甘、乌鲁瓦图和塔纳洛特等地都有极其壮观的海边庙宇保护人们免受邪恶力量的伤害。在巴厘岛的中心地区,有不同等级的庙宇。按照崇拜的团体来划分,有家族的庙堂、村庄的祠堂以及地区的庙宇,最后还有庙宇之首——贝沙基庙。它建在阿贡火山高高的山坡上,台阶和梅鲁阴沉的黑色塔顶直入云霄,俯瞰着人类世界,同时指向高远的天空。朝圣者从海上一路向上攀登,最终来到他们的世界中心中最崇高的地方。
在巴厘,艺术和自然互为倒影,正如相对放置的两面镜子。基本的主题从自然风景中锤炼;赋予其社会意义之后,在房舍、庙宇和村庄中加以复制。反过来,它们又变成理解的方法,引导人们在这个以山为中心的封闭世界里栖居。我们这些人并不生活在以这个美丽的热带岛屿为基础形成的传统封闭的社会里,因此无法拥有如此清晰、确切、无所不包的统一风景。但是,我们可以收集我们的资源(不管多么少),使它们集聚在一个场址上(无论多么小),以构造一个清晰的片断,在花园里打造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