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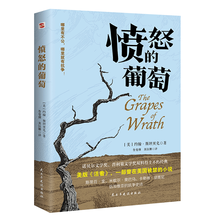



1 凯瑟琳·媞卡薇瑟,你是谁?
你可是生于一六五六年逝于一六八○年的那个女人?难道这些就够了?你是易洛魁人①的圣女么?你是摩霍克河畔的百合么?我可以以我的方式来爱你么?我是个老学究,我的脸因为屁股久坐的缘故少受风霜侵袭,如今的相貌比起青葱岁月的我倒更好了。我来寻你,我想知道那玫瑰色毯子下到底在发生什么?我有这个权利么?我爱上了你的圣像。你站在我最喜爱的白桦树之间。上帝才知道你鹿皮软靴上的饰边有多高。你身后的河肯定是摩霍克河了。左边地上的那两只鸟,如果你轻挠它们的白脖,甚至在某个寓言里将它们作为比喻,它们定会因此而欢悦。我的心沾满了灰尘,拥塞着几千本书的谵言妄语,若是如此,我有权利来寻你么?我几乎很少出门去乡下。你能教授我叶子的学问么?你知晓能引起幻觉的那些蘑菇?玛丽琳几年前过世了。说不定四百年后的某个可能和我有血亲的老学究来寻玛丽琳这个女人的历史,就如同我寻你的历史。但眼下你必须对天堂了解得多些。天堂看起来是否像夜色中闪光的塑料祭坛?我发誓,即便果然如此我也不在乎。我们肉眼能见的那些星星毕竟很小,不是吗?一个老学究能否最终找到爱,不用每晚自慰才能入睡?我甚至不再恨这些书了,读过的书我也忘了大半,实际上,这点对于我或者这个世界都无足轻重。我的朋友F吸高了大麻后总兴奋不已地说:“我们必须学习勇敢地停留在事物表面。我们必须学习爱事物的表面。”F死在精神病院某个墙壁四周加了软垫的病房里,他做爱太多,淫乱不堪,脑子烂了。我亲眼看见他的脸色变黑,他们告诉我他的老二基本废了。有个护士告诉我他的老二看起来就像一条蠕虫的内部。向F致敬!这喜欢大声嚷嚷的老朋友!我怀疑你的记忆是否能持久。而你,凯瑟琳·媞卡薇瑟,如果你必须知道,我如此人性,以致要忍受便秘——这惯于久坐而带来的馈赠!我的心早已飞到白桦林,这有什么奇怪吗?一个穷困潦倒的老学究想爬进印有你图片的彩色明信片,这有什么奇怪吗?
2 我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民俗学者,研究A族人的权威。A族,我无意用我的研究兴趣让这一族人蒙羞。A族可能只剩下十个纯粹血统的人,其中有四个还是十来岁的姑娘。我还得说F利用了我的人类学研究为口实操了这四个姑娘。老朋友,你罪有应得。A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族群残留下来的后裔,似乎在十五世纪就出现了。它简短的历史充满了连串的挫败。而他们的族名——A,在与其比邻族群的语言中意为尸体。在有记载的族史里,这个不幸的族群从未赢过一场战事,而在它敌人的传说与歌谣里却满是胜利的嚎叫。我对于这个充满了彻底失败的族群的历史兴趣盎然充分显露了我的性格。F每每从我这借了钱,他总会说:“多谢,你这个老A——!”凯瑟琳·媞卡薇瑟,你在听吗?
3 凯瑟琳·媞卡薇瑟,我要来救你出耶稣会。是的,老学究就是敢想。我不知道如今他们如何对你说三道四,我的拉丁文早不灵光了。“只要我们的希望获得了成功,在祭坛上就能看到你,一个易洛魁族圣母,加拿大的烈士——烈士的玫瑰,处女的百合。”这是耶稣会一个叫Ed.L的人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写的一条短笺。但是这有什么关系?我可不愿在去往摩霍克河的旅途上仍带着往日争强斗胜的回忆。掌握好节奏!耶稣会!F曾说:“坚强的人只爱教会!”凯瑟琳·妮卡薇瑟,如果他们把你做成石膏模子,我们会在乎么?我近来正研究用桦树皮造独木舟的图纸,你的族人已经忘了这门手艺。如果蒙特利尔每辆出租车的仪表板上都挂着一个你小小身子的塑料像,你会怎么想?应该不会是件坏事Ⅱ巴。爱不能储存。每一个从工厂制作出来的十字架上是不是都有耶稣的痕迹?我想是有的。欲望改变世界!谁将漫山的枫叶变红?别吵!你们这些生产宗教小饰品的家伙!你们是和圣洁的事物打交道!凯瑟琳·媞卡薇瑟,你瞧见我就这样失控了么?你知道我多么希望这个世界神秘而美好?我们肉眼见到的这些星星到底是很小的,不是吗?谁送我们入睡?我该不该保存剪下的指甲?物质是否神圣?我想让理发师埋掉我剪下的头发。凯瑟琳·媞卡薇瑟,你是否已经作用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