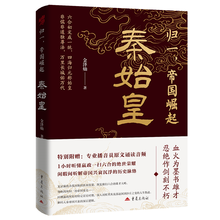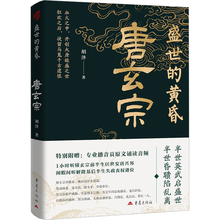然而,这样的困厄,并未打消杨广的游兴。他携着萧后及众贵妃、美人继续巡幸作乐。被异族围困的耻辱和四处燃起的烽烟,早已抛诸脑后,他甚至连勤王解围的将士也未予奖赏,便从容南下江都。
李世民在云定兴军中逗留,约有年余,见主帅未蒙天子赏赐,自己也就识趣地打消了得到提拔重用的奢望,原有的一番报效隋室的激情,顿时化为乌有。联想起近年来隋主荒淫失政,佞进贤避,天灾人祸不断,百姓生灵涂炭的现实,以及父亲因姓李而屡遭猜忌贬斥的背运,尤其是近年来,天下广为流传的童谣“桃李子,有天下”,常令李世民生起一股莫名的忧惧和冲动。
他不禁心绪浩荡,萌生退意,打算先回乡游学访友,以观时势。主意已定,便辞别云定兴,回到父亲府中。
此时,李渊已担任太原留守。经过他的苦心经营,太原已牢牢控制在他手中,俨然成为他进退自守的根据地。李世民在太原仗义疏财,重诺好施,广结豪侠俊杰之才,日日与饱学之士相接,故虽年少,却有不少豪杰文士汇集门下。
其时,炀帝在江都昼夜行乐,天下草寇纷纷占山为王。河北高阳贼首魏刀儿,自号“历山飞”,在太行山一带打家劫舍,攻城略地,远近闻名。
这年春天,魏刀儿又率数万喽罗,前来攻打太原。李渊亲率骑兵,突袭敌阵,不料孤军陷入贼阵重围,难以脱身,情况万分危急。幸而有逃出的军士回城禀报。李世民得知情况,心急如焚,仗剑跃马,率数十轻骑突入重围,弯弓搭箭,矢无虚发。贼兵上前阻挡,无不应弦而倒。
敌阵被世民轻骑撕开一道裂口,李渊趁机杀出重围,然后召集大军,回马与世民夹击贼兵。一时间,贼兵陈尸遍野,魏刀儿只带少数几个随从逃得性命。经此一战,太原渐渐安定,远近盗寇,不敢轻易扰掠。
这一年,李世民十八岁。
解救雁门之围和抗击魏刀儿,李世民初露锋芒,战无不胜,威名远播。这既是对他幼时所学兵法及骑射技艺的检验,也是作为关陇贵族所推崇的尚武精神的一种折射。
在世民同胞兄弟四人中,三弟玄霸早夭,兄长建成、四弟元吉和世民接受着同样良好的儒学和武术教育,也同样经历了父亲遭受猜忌时的坎坷耻辱及军旅生活的艰苦磨炼。所不同的是,建成性格宽和柔顺,元吉狡黠顽勇,二人巧于侍奉亲长。意志力均不如世民。而世民则不仅聪慧慎思,且喜读兵书,个性坚强,勇猛决断,又善结交朋友。因而,早年战争阅历中表现出的卓越军事天才,已不仅仅是激发他“济世安民”的英雄壮志和自信力的催化剂;如果再加上生为次子这一不幸的排行,便注定了要由他主演用兄长的鲜血祭奠自己宝座的这一出带有必然性的悲剧。
炀帝在其末年,他那劳民伤财的远征和恣意淫乐的巡游,耗空了国库库银,繁重的赋役和黑暗的统治,逼得百姓纷纷落草为寇。地方豪强也趁机拉起人马,攻州掠县,称王称霸。到大业十三年(617),单单有名有号的叛乱者,就有近五十处。
其中,尤以河南瓦岗的李密、河北的窦建德、淮南的杜伏威、马邑的刘武周、河西的李轨、金城的薛举、巴陵的萧铣、曹州的孟海公等,声势最为浩大。每处人马,数十万、上百万不等。
此时的炀帝,却被宇文述、裴矩、虞世基、裴蕴这帮专门报喜不报忧的佞臣所包围。他们将各地郡县告急的文书一律压下,而禀报给炀帝的却是“盗贼渐少”。炀帝恰好也不爱听“盗贼日多”的坏消息。于是,君臣相欺,佞臣们忙于弄权,而炀帝则乐得与萧后等一班宠妃寻欢作乐。眼见着大好江山,日渐沦丧。
大业十二年(616)冬,李渊因为剿匪有功,被正式任命为太原留守,负责太原以北地区的防务,以阻止突厥人南下侵扰。
李渊对于这一任命喜不自胜。他不由得想起一年多前,他任河东慰抚大使时,自己的副手大理司直夏侯端的话。夏侯端曾对李渊说:
“在下近日夜观天象,玉床摇动,帝星不安,而岁星居于参位。参宿为晋阳分野,这不正应在阁下身上吗?如今圣上猜忌残忍,对诸李姓尤为防备。郧公李浑才被处死,阁下若不思通变,必定成为李浑第二。”
李渊心中深以为然,但因为种种顾忌,表面上不敢有半分不忠的表示。他总觉得当下之计,是先脱离险境。现在他正式成为太原的最高军政长官,觉得自己终于彻底摆脱了因“桃李子,有天下”的图谶而引起的炀帝的猜疑和防范,起码远离了因姓李而面临杀头的危险。
自大业十一年(615)赴河东剿匪,到如今被正式任命为太原留守的这两年时间,他的军队一直驻防太原。经过他的苦心经营,太原已被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可以说,此时的太原,已成为他进退自如的根据地,足以抵御来自任何方面的挑战。炀帝的任命,只不过是不得已的对李渊军事实力的事实上的确认。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内心隐隐觉得自己以唐公的爵位,担任传说中圣君唐尧的发祥地太原的长官,是天命所归,是上天有意成就他,树立他。
这个想法使他惊惧,更使他激动。这种按捺不住的喜悦,使他不无野心地对次子李世民说:
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取,祸得斯及。
而李世民此时走得更远。他未雨绸缪,疏财仗义,结交扶助各色豪杰。
他知道父亲对炀帝猜忌的不满和对杨氏政权的失望,但他也知道父亲的瞻前顾后和隐忍不决。因此,他深深明白,如果没有来自内外的推力和压力,父亲的抱负也永远只是想法。因此,世民在等待适当的时机。
这期间,李世民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婚礼。他娶了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为妻。妻兄长孙无忌也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妻子的叔叔、右勋卫长孙顺德,左勋卫刘弘基因逃避征高丽的兵役,此时正亡命天涯,被李渊收留。他们和李世民交往密切,得到他的多方照应。左亲卫窦琮也流亡在太原,但因以前与世民有过节,常常心存疑惧。世民却并不以从前的嫌隙为意,反而友好地与窦琮交往,出处饮食,亲密无间,令窦琮感激释怀。这使世民轻财好士、宽怀大度的声名广为传播,并传到晋阳令武功人刘文静的耳中。
文静姿仪倜傥,器宇不凡,平生自负才略,轻易不肯服人。他总觉得李世民乃贵家公子,少年逞豪,声名恐怕言过其实,便想亲自考校一番。
这一天,文静乘赴留守府公干之机,径自踱步到世民住处,自报了名姓。世民一听,是晋阳令相访,也久慕其名,连忙下阶相迎,礼节备至。二人略事寒暄,便转到当今朝廷政事。一番探讨,互相叹服英雄所见略同,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