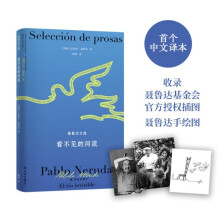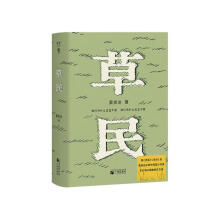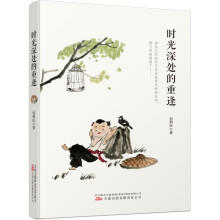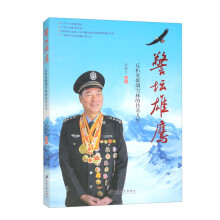皇甫浞亦韩门弟子,投入韩门虽较晚,却最得韩之器重——韩曾嘱皇甫于其死后为作墓志,由此可以看出韩传衣钵于皇甫浞而非李翱;从而可见韩愈所重毕竟在文,韩文特质毕竟在奇。虽然李翱的排佛不够全面,但在对佛教教迹的反对上与韩全然一致,韩不传李,证明他重“文”不重“道”;李翱倡平易自然之风,皇甫浞则尚奇崛,韩愈传皇甫,证明他重奇不重易。至于皇甫浞对佛教的态度,最可能的还是并不在意;换言之,排或不排,似不措怀。虽然皇甫浞有《送简师序》,对简师佛名而儒行、夷狄其服而仁义其心、不满于韩论佛骨而遭贬而浮屠之徒欢快以忭的行为表示难能可贵,又有《送孙生序》,对孙生于天下胥化佛法的情况下独发愤着书、攻而指斥表示推重,似乎反映他也是排佛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简师将适潮州访韩愈而求序于皇甫,皇甫又岂能不为序予以肯定之?孙生斥佛与其师韩愈一致,皇甫又岂能不推重之?换言之,二序的写作都有其特定背景,固不足以论断其排佛。何况皇甫另有《庐陵香城寺碣》,其中说道:“炅师作主,亘公来禅。大饰图像,益崇榱椽。百祀来胜,江山助妍。宜序于铭,以刻于坚。既序既刻,光流亿年。”颇美佛寺之经营而愿其永恒。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