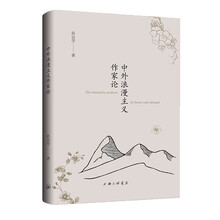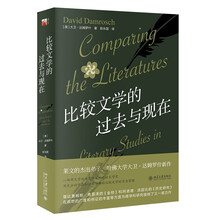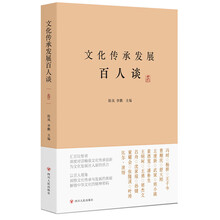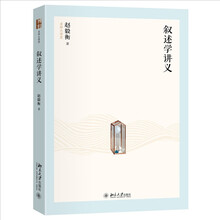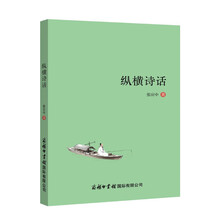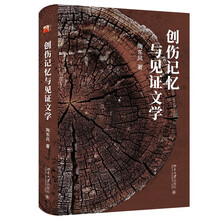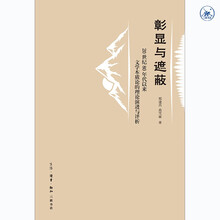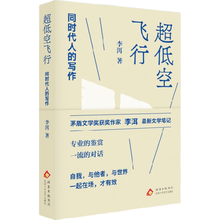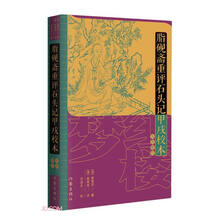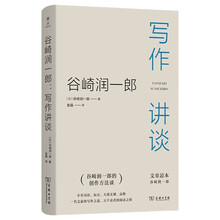这个年代必须与今天之间存在着一个分界。就是说,个体的悲剧性遭遇总是能够溶化到历史的喜剧性结论中去。战争结束了,人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候,似乎很少有艺术镜头对准那些永远失去亲人的悲哀者面孔和永远破碎了的家庭。同样,在一场浩劫以后,人们为一些终于平反昭雪者写传时,总是为他们的苦尽甘来而欢欣,却少有人注意到他们永远失去了的健康、青春、理想、甚至幸福……巴金《随想录》的文学价值之一,就是它塑造出一个永远孤寂凄凉的老人的自我形象,而这种美感形式在战时文化背景的制约下往往是难以被接受的。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的。胜利者愿意自己的成功成为某种历史性转折的标记,愿意看到历史在自己的成功处出现一个句号。某些作品之所以受到批评,正是因为它把个体的悲剧性价值从历史的喜剧性结论中分离出来,它让个体生命的悲剧如一道水流淹过了固定的历史句号,从而违背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文化基调(如《苦恋》)。
虽然有人赞美我们的民族酷爱和平、讲究中庸、具有非战的传统,虽然也有人批评传统文化的束缚造成了我们民族的孱弱、保守和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以至缺乏开拓进取精神,但有一点似乎很少被人注意到,中国文化传统中始终掺有古代兵家思想因子,重视兵法和战术的研究。它渗透在各种学术思想之中。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