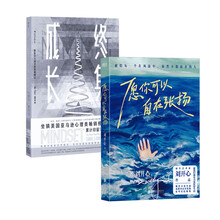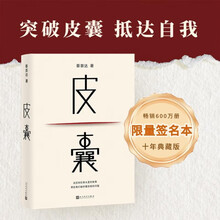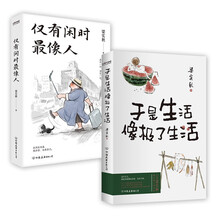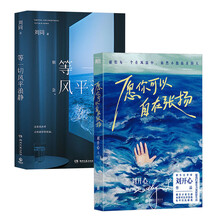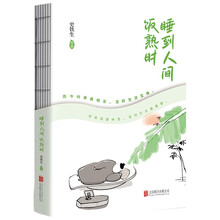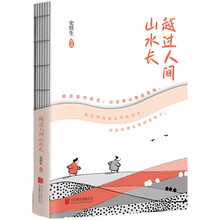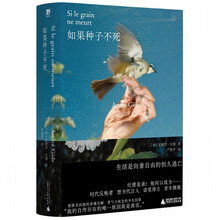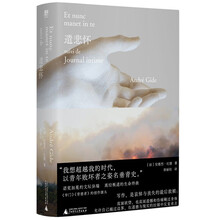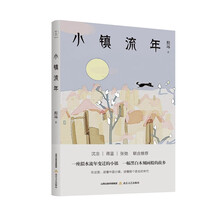“E.B.怀特随笔”由作者本人选定,囊括了这位最伟大的随笔作家最重要的随笔作品,中文版分为两卷出版,第一卷名曰:《这就是纽约》。其中《这就是纽约》系怀特最为知名的随笔作品之一,1948年,《假日》杂志上全文刊登了这篇散文,此后不久,又出了单行本。2001年,经历了9.11之后的美国人再度翻开了这本书,发现五十三年前他们根本没有读懂这些铅灰色的预言:“纽约最微妙的变化,人人嘴上不讲,但人人心里明白。这座城市,在它漫长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只须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摧毁桥梁,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将数百万人化为灰烬。死灭的暗示是当下纽约生活的一部分:头顶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噩耗。”
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E·B·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