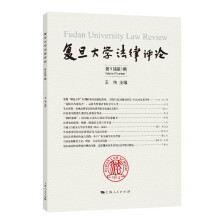(1)第29条究竟是共犯独立说或是从属说,本身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刑法》第29条教唆犯的定义明显表明,第1款采纳的是共犯从属理论;第2款的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依照目前对于共犯从属采有限从属来看,第二款的规定对于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共犯却可以处罚的情形,事实地让教唆犯既遂的时间点前置,因此第二款跳到共犯独立性的理论状态。笔者认为,《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有点相似于台湾地区2005年“刑法”修订之前对于“被教唆人虽未至犯罪,教唆犯仍以未遂犯论”。只是,台湾地区对于教唆犯在修法前的认定都是极端的从属形式,基于阻吓恶性较大之教唆行为人,对于被教唆人虽未至犯罪(也就是不到极端从属的形态)依然有限度地将一些犯罪的从属形式提前到不法以前,为了控制是对于恶性重大之教唆限度,特别以“但以所教唆之罪有处罚未遂犯之规定者为限”限定之。因此,台湾地区旧的教唆犯规定,始终没有脱离共犯从属的框架,甚至是因为严守共犯极端从属形式而以特别规定的方式,将恶性重大的教唆犯既遂时间点提前,但依旧谨守从属的大原则。反观《刑法》对于“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之文义解释,被教唆的人没有犯所教唆的罪这样的表述,让教唆犯着手的时间点无限前置,应该理解为教唆犯教唆被教唆者后,教唆犯即成立(因为被教唆者没有犯,教唆者亦可被处罚),面对法典的解释学上,文义解释应该是处于至高无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因此教唆犯在文义解释上面就是脱离了共犯从属理论的框架。面对第1款与第2款互为矛盾的状况,最理性的实践态度是,不再对这两款进行任何超出文义解释的任何解释,因为这只会造成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应谨慎操作。至于,第1款共犯从属性的实践部分,应存在于,在共犯如何成立的问题上,应采用有限从属形式,也就是对于共犯的成立程度,以及对于共犯赋予责罚的范围,采有限从属标准以界定。而对于第2款的规定,笔者推想,当初的立法者应该是认为教唆犯本身的恶性重大,并且立法者对于教唆犯法益破坏的思想,是认为在一开始教唆就破坏了法益,而不问最后被教唆者是否真的实行,或是不问被教唆着所实行的是否是教唆之罪。对于这样的想法,笔者认为,支持立法者对于阻却恶性重大之教唆犯的苦心,但是,因为这样的第1款和第2款条文的相互冲突,导致了教唆犯的条文不稳定的结果,笔者建议可以修改第2款的规定,将第2款修改到较符合共犯从属形态的状态。
(2)对我国大陆《刑法》第29条第1款的回应。笔者已在前面对于第1款的规定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存在从属问题提出看法,如果依照我国目前学说对于解释教唆犯一致认为教唆犯目前是有限从属性的范围,前半部分对于犯罪的理解应是不法。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