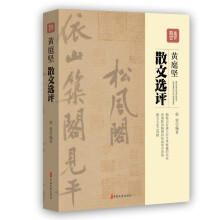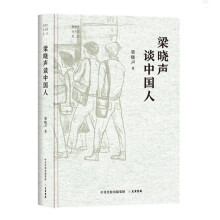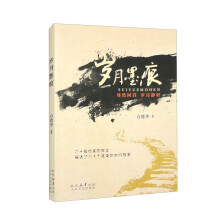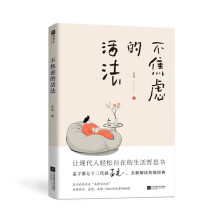都找到了! 话说当天在宋以朗家里,止庵看了看张爱玲给“斌”的钱包和谢卡, 也没说啥,话题就转到别处,大概是谈关于《异乡记》手稿在中国大陆的 出版策略,大家兴高采烈,好像要替张小姐办喜事。 宋先生大概是这样的,或所有人都必然是这样的,谈得愈有兴头,他 便愈有意愿从房间里掏出更多的张爱玲宝物,一旦话不投机,匆匆看过例 牌式的几个东西,便送客了。所以那天宋以朗又从房间找出一个大大的牛 皮纸袋,解开绳子,把袋倒转,跌出一大叠零零碎碎的纸张纸条,包括拆 开了的自信封,由《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或“皇冠出版社”寄出的; 撕下来的报纸版面;正方形的memo纸;废弃的稿纸边缘……出处各异,但 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变成了张爱玲的草稿纸,可见她昔年在美,随时随地想 到什么,随手抓起一片半页纸张,立即执笔写下。 张爱玲非常环保?我暗暗认为,这或跟环保无关,而是她不愿错过任 何于刹那间闪过脑海的意念,担心善忘,急急透过书写这种动作把它记牢 。又,她是作家,对于纸张总有过敏性的怜惜,纸是亲人也是朋友,人浮 于世,至少在那年头,纸张往往是最能令作家有安全感的身边物件。 而小巧合就出现在纸张之上:那天我随手从那凌乱不堪的纸叠里抽出 一页,是拆开了的信封,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定神一看,无巧不成书, 最后一段写的竟然正是张爱玲写给“斌”的短信草稿,跟她在正式谢卡所 写的有九成符合。对于写字,张小姐确是认真严肃,连在谢卡上写几十字 都要先打草稿,到了真写,还再改动一次。 于是在我眼前桌上并排放着谢卡和信封,张爱玲的心思曾经在两者之 间流转波动,它们展映了时间的痕迹,如同呈现一位动态的张爱玲。 两年前带陈子善往访宋以朗,送回第一个钱包;两年后带止庵往访宋 以朗,找出其他钱包的主人。三个钱包都被解谜-了。陈子善和止庵都很高 兴,但最高兴的人,其实可能是我。因为我不仅意外地撮合了陈子善和止 庵替张爱玲完成钱包遗愿,连随手在张爱玲留下的一堆草稿里抽出一张纸 亦跟钱包遗愿有关,谁敢否认,我才是这次“遗愿完成仪式”的“灵魂人 物”? 我向爱捣蛋,两年前我曾对陈子善开玩笑道“依这事看来,爱玲还是 爱你的”,所以两年后我特地再捣蛋一次,眯起眼睛对止庵说:“依这事 看来,爱玲原来最爱的是我。” 止庵没反应。我可不管他和陈子善怎么想,反正人生苦短,懂得讨自 己开心,最重耍。 你,抑或你们? 每回张小姐的出土作品得见天日,我阅后,例必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宋 以朗,对他说,大佬呀,唔该你加快动作,足不出户,把张爱玲档案结集 ,好让我们对她的心事与私事与笔事知道得更多一点、更多一点。 电话那头,宋先生总只腼腆地笑笑。或许在通话的那一刻,他正坐在 客厅的长桌子面前,双手把残稿断章覆来验去,像法医官一样,或更像考 古学家,欲把最新挖掘出土的文物重新拼凑成一幅渐行渐远的繁华盛景。 忙累了,宋以朗,然而愈忙愈好,黑心地也好心地,张迷们“祝福”你无 日得闲。 宋以朗忙碌成果之一是于今年书展现身的《张爱玲私语录》,收录了 比旧版多出一半的张氏金句,亦有她和宋氏夫妇的私密通信,尽管经过节 录筛选,却仍令普罗张迷或专业研究者同时读得入神入味。也值得高兴的 是,宋先生于前言表明他们仨的“书信全集正在整理,将于日后完整出版 ”。唯望尽快,而且誓要补回那被筛走的部分,甚至应该考虑以原始档案 形式留存于某个研究机构供有心人尽览全豹。 新旧版的张爱玲语录,除了内容数量有别,某些字句亦稍为异动,所 以读时,别偷懒,必须看注。 像《秧歌》在美国出了英文版,张小姐心情亢奋,新版语录写的是: “本来我以为The Rice-Sprout Song的出版,不会像当初第一次出书时那 么使我高兴得可以飞上天,但是现在照样还是快乐。我真开心有你,否则 告诉谁呢?”旧版的“你”是“你们”,意指不止于邝文美而更包括宋淇 ,但新版的注清楚地表示,手稿原文确只是“你”。一字之变,已够让张 迷玩味一个晚上。 为何把原稿的单数“你”变成旧版印行的复数“你们”?是宋淇当年 在编辑审稿时,心里吃醋,觉得“我也跟张爱玲很要好啊,怎可能遗漏了 我”而擅自加入一个“们”字?抑或邝文美爱夫心切,担心丈夫吃醋,主 动在帮忙审校打印稿时在校样上把他夹带进来?张爱玲呢?她自己心里到 底怎么想?你,抑或你们? 乱世里的文人友谊,本身就像一出精彩的戏码,高低起跌,变幻无边 。新版语录铺陈了三个人的深刻情谊,我们能做的只是隔世羡慕,以及, 景仰。P18-21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