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归来》令我们想起另一位也是从东欧到了西方的作者,昆德拉。昆德拉的写作其实是两块的,不只是因为他到法国后改用非母语的法语来写作,也因为移民、离开母国经验对他造成的影响。他用法语写作的作品——包括文论和小说,《帷幕》、《身份》、《缓慢》等等(自昆德拉开始,我一直把文论和小说当作同一种东西来读,包括其后陆续翻译成中文的库切、奈保尔、拉什迪乃至艾科,有时候,甚至包括齐泽克的电影和黄色笑话分析。真是奇怪的经验),跟他早期《告别的聚会》、《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这些在捷克、用捷克文写作的作品有很大不同。
马内阿和昆德拉一样的是,他也离开了母国,移居到了美国。如果移民前的母国经验,与移民后的西方经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则马内阿的返乡、及将返乡经验写成的《流氓的归来》,联系了这两个世界,相当于把昆德拉在捷克和去法国后前后两边的经验结合起来了。由祖国到西方而又回到祖国,离开与回归,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圈。对写作者马内阿而言,这是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对读者而言,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阅读经验。
但返乡并不等于返回离开前的家乡。在时间中,家乡已经变化了,写作者也变化了。经过一个移民者的、流离迁徙的经历,看待家乡的眼光也不同了。马内阿对罗马尼亚的认识获得了一种相对来说不那么情绪化,更为沉静的眼光。书中充满对罗马尼亚那段现实很精微的回顾。这仿佛是一种淘洗的过程。抽离,回归,再抽离,再回归……人在这个过程中淘去情绪化,获得对身处现实的一种沉静的理解。米兰’昆德拉曾说:“为了能够听到隐密的、几乎听不到的‘事物的灵魂’的声音,小说家跟诗人与音乐家不同,必须知道如何让自己灵魂的呼声保持缄默。”我想有时人生经历正是使小说家获得这样一种灵魂的缄默,与沉静眼光的方式。
马内阿在美国时,曾经和索尔·贝娄谈到想回罗马尼亚的念头,索尔·贝娄劝他不要回去,但最后马内阿还是决定回去了。马内阿说因为老朋友在招他回去,他说:我是因为“友情的专制”才回去的。“友情的专制”,一个微妙的、放射性的说法,他是为了故人而回去的。人离开了故乡,但是很多人的关系还是割舍不下。就像他在母亲死后九年才终于能回乡上坟。离开是为了政治的专制,回乡是因为人终于还是脱不开故人与故土,这也是一种专制,是与生俱来的牵绊。
至于劝他不要回乡的索尔·贝娄,本身也是俄国犹太人后裔,父母在二十世纪初移居美洲,也是上世纪人类离散经验的见证者。但贝娄毕竟是出生在美洲,并没有一个故土。他与马内阿还是不同的。马内阿的经历是他自己的,最后做的选择也纯然是他自己的。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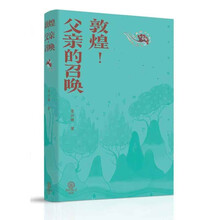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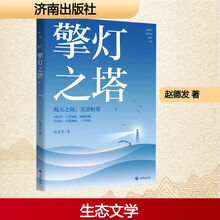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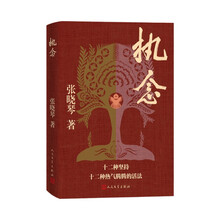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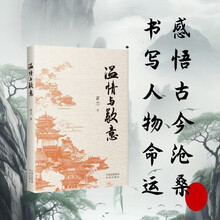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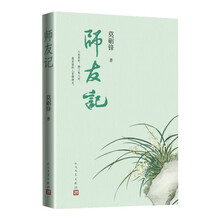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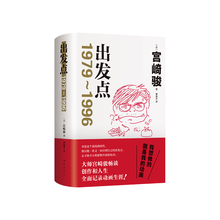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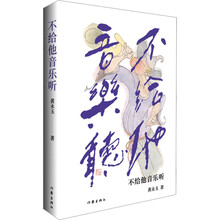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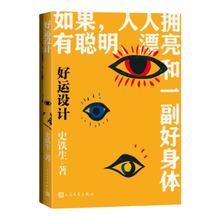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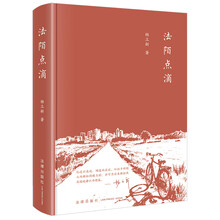
——毛尖(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