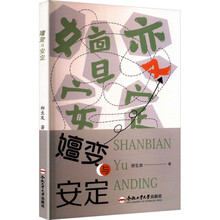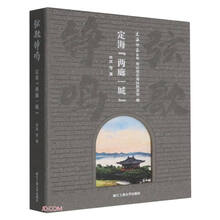我目睹过一个非常坚强的生命,不在战场,在病房。
他是刚刚步入中年的男人。据说,患病前他是当地一位非常有前途的中层领导,可偏偏在那个时候健康状况出现问题,而且是很不容易修理的问题,他不得不放弃仕途,先后转辗于各大医院寻求最好的治疗。
他的病情好好坏坏、反反复复,已经接受过大大小小许多次化疗了,当入住我们医院的时候,他的病程已经有3年多,疾病到了晚期,双腿无法灵活运动。
如果没有这场疾病的光临,也许命运将会带给他另一番令人羡慕的情景。然而,命运这个东西真的让人始料不及。
在病房的几个月里,我天天目睹他与疾病抗争的每一个细节和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精力一点点消耗、活力被一丝丝吞噬,男人所特有的英气也一天一天颓败下去。
最终,他无法抵挡病痛压倒一切的强势,静静地走了。
记得那是一个初冬的上午,金灿灿的阳光依然随意地洒在他白色的病床上,洒在他惨白的脸上,他静静地走了,我相信他是带着温热的阳光走的。
做血液内科医生多年的我,目睹他历尽磨难、在平静坦然中接受生命遭遇的每一次致死性打击却依然意志坚强,我为他的刚毅所感染,至今没有忘记。
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们科里几个医生说起这位病人在生命最后一个星期的情况,心底仍会涌动起一阵阵感动,对逝去的生命充满敬意。
此刻,我用文字记录下记忆中这个病人在生命最后日子里的点点滴滴。
起先,他是后腰部疼痛,不能久坐,排尿有些费力,核磁检查发现他的脊柱旁有一个团块影。对这一发现,我们医生们都感到非常棘手,因为外科医生会诊的结果是——那个团块很难手术解决。
也许,最后的日子就要来了。这种念头不仅在我们医生的脑子里出现,同样在患者和他家属的脑子里出现。
“大不了与肿瘤同归于尽。”这是他常对我们说的一句玩笑话。
后来,他的双下肢不能动弹了,他成了双下肢截瘫的人。每天治疗结束,他安静地坐在轮椅上,紧靠着窗边,窗外透过来的温暖阳光洒在他的脸上、身上,他时常捧一份报纸或杂志,默默地读着,有时也想象外面的精彩世界,有时闭上双眼享受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阳光沐浴。
后来,他的每一个器官都不太对劲儿了,肝脏功能减退,心脏功能不全,肺里总是不断生出各种各样的细菌、霉菌,随痰液大口大口吐出,他的精力不足以支撑他长久坐轮椅,大多数时候他只能躺在床上。
最后,他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他能体会到那些病症匍伏在体内,毫无阻挡地继续向上缓缓蔓延,蔓延到他的后背、前胸,蔓延到他的双侧上肢,这些部位的肌肉像中了邪似的瘫软,无法用力,他成了地地道道的高位截瘫病人。
我们检查他上肢的肌力,将他的上肢举起来,然后松手,他的肢体便软软地、沉沉地坠下,重重地落在床上。我们检查他的感觉,用稍尖锐的针头轻轻刺他的皮肤,他竟然一点痛觉也没有,他的躯干和四肢完全失去运动和感知能力。他说,若他的肢体有疼痛的感觉该多好,疼痛,对他来说变成了奢侈的事。
他在床上躺着,一点儿也不能动弹,像一位被捆绑者毫无自主活动的余地。他无法翻身,无法坐立,无法握住任何一件哪怕轻得像纸一样的物品:他无法感觉,没有触觉、痛觉、温度觉;当然他也不再有便意,无法自行排尿和排便,以致我们不得不给他插根尿管定期排放尿液。他全身唯一可以活动的部位就是头部,他本可以说话的,但因为咳痰不畅、呼吸肌无力,不得不在喉部切一个小口,经气管切开插一根直径2公分左右的特殊管子与呼吸机连接,目的是机械通气辅助他的呼吸。这样,他的头部就不能随意摇晃,嘴也无法说话、不能吃饭了,我们又只好从他的鼻腔插一根橡皮管直抵他的胃里给予鼻饲,用注射器将流质或极稀的糊状食物通过这条橡皮管送到他的胃中,以解决他的一日三餐问题。他的身上还有一根细细的管子插在静脉里,主要解决静脉输液用药问题。数数他身上,粗粗细细已经有了4根不同功用的管子。
逐渐地,他的自主活动区域又缩小了许多,只剩下面部一些肌肉和一双能随意运动的眼球。他同我们交流,是通过这一点点所能控制的肌肉活动来实现的。
每一个问题的对话常常要花费大家几个回合的沟通,如果他有不适或其他要求,比如他想动一动身体、抬高一点枕头、有口渴或饥饿感以及其他身体不适等,我们或他的家人便要猜测,然后问他我们的猜测对不对。对了,他就向我们眨一眨眼,大家便付诸行动,若不对,他就用一双眼睛盯着我们或稍微晃动一下脑袋,示意我们没有说对,于是我们又重新开始“对话”。
他以那样的姿势、状态一直坚持着、努力着。也许,还有回忆和思考。
我们真心希望他舒服点。
他的生命比我们料想的更长,他的坚持和顽强令所有的人震撼。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