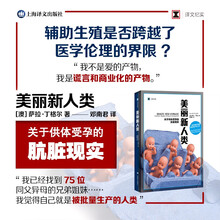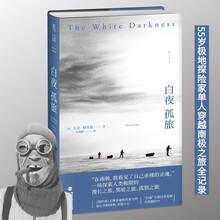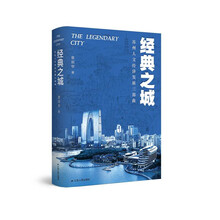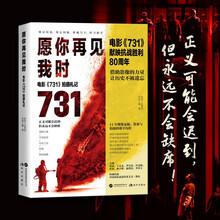一、往事回首,从初为人母说起
窗外是无边的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无际,无垠。大自然又一次恩赐给人们一个洁白的世界。就连附近林子里的大小树木也都银装素裹。一抱粗的大树显得更加挺拔,愈发与众不同,分外娇娆。树林对面冬天。远眺雪后从我家通往实验室的小路的小山坡上,那排红砖瓦小洋房的篱芭,本来是各有千秋的,眼下却变成了清一色高高低低的白墙,它们和那些房顶上厚厚的积雪一起融入了浩渺无际的苍穹。
我家门前的那条石头小路上,还没有留下任何足迹。平时,林子下面、牧场里的动物比人勤快得多。拂晓,公鸡开始报晓,它俨然以家长的姿态带领大大小小“子女们”,窜到每户人家的花园里,总能寻得满意的美餐。住在那排小洋房里的黄猫和黑猫是一对情侣,尽管它们都接受了节育手术,还是只要一有空就会呆在一起,形影不离,相互追逐。它们总是一起躲在有太阳的墙边打盹,每天如此,除了主人的呼唤和那条叫杜米农的大狗的吓唬,谁也分不开它们。这样大的下雪天,它们没有在一起,定是各自的主人不允许它们出来,因为那条叫杜米农的大狗已经在一年前病死了。
我坐在窗前享受简单的早饭,一个羊角面包、一杯热牛奶和一个苹果,盘算着今天要不要去实验室。沿着门前这条石头小路,穿过两个停车场、一个农庄旧址、一个网球场和一个小花园走过马路就到了,我的实验室就在那座银灰色的长方形大楼里。我的小办公室在大楼四层的东南角儿,一台计算机把我和广阔的世界连在—起。用计算机上网,可以使我进入一个属于自己的浩渺无际的科学、文化、艺术世界。用计算机写作可以使我如醉如痴,留恋过去、畅想未来,全然忘却了今夕是何时。此刻,我能感到的只是自己在上下求索中充实、壮大、提高和升华。就是这样,我在这里,这个美丽的西欧小国——比利时已经度过24年了。
泡上一杯浓浓的香茗,打开计算机,便进入了我的写作世界。一个完完全全属于我的世界。我用英文或法文撰写科学书籍、论文和报告;用中文记述自己的人生阅历和一个母亲为了重塑爱子奋力拼搏所经历的种种失败,以及从中所感受的种种苦辣悲欢。我总是尽可能把属于自己的时间、精力,都放在那个属于我的世界里。
1.我有了个很可爱的儿子,小欣欣
1968年的秋天,我乘轮船沿长江从上海出发,到重庆等地出差。白天,一路饱览三峡险峻旖旎的风光,尽享两岸柑橘绿树茂密葱郁,满挂着黄橙橙果实的绝妙美景。我想象着那些红衣蓝裤、背竹篓的姑娘和穿运动衣挑担子的小伙子们,三五成群往来在山中的羊肠小道上,嬉笑间流淌着快慰。夜晚,静观两边山川峡谷之间,在万里无云晴空中悬挂的一弯明月,倾听那浪搏山岩、水溅船舷的独特交响音乐。真是犹如置身.于世外桃源,让人陶醉、让人梦幻。在这天堂般的境地里,会让人暂时忘却了种种人间争斗和不曾完全熄灭的硝烟战火。
船行到玉女峰下,美好被一阵晕眩和随之而来的呕吐打破,白天的食物都完全吐净了。怕是晕船和疲劳所致,我回房简单洗漱之后,赶紧躺下休息。到了重庆呕吐现象更厉害了。从重庆坐火车到成都以后的五天,只能喝水或吃一点柑橘泡菜之类的食物。奇怪的是,呕吐之物有明显苦味,我并没有吃任何苦味食品。一位近五十岁的成都饭店女服务员要我别着急,她说你大概是有喜了,她送来一碗为我特别煮的藕粉。天啊,我要做母亲了!我有点措手不及,毫无思想准备。我决定等回上海证实后再告知家人。
回到上海,怀孕的反应逐渐减轻。朱月明同志(所里的人事部门负责人,一位很热心、很平易近人的新四军转业干部)对我说,我已经到了该有孩子的龄了,夫妻分居两地要小孩虽有困难,但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她还说大家都会帮助我的,她要我吃好、睡好,有任何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她。我的家人得知这个好消息都很高兴,他们的意见也都和朱月明大同小异。于是,我的生活又走上了常规,只是休息的时间多了一件事,为小宝宝准备各种必需品。我也像所有第一次做母亲的人那样,小心而好奇地享受各个时期的愉快,毫无怨悔地对待各个时期的困难。我把那个藏在体内的小生命当成了自己最知心的朋友,无话不谈。他的存在让我感到自己有了家,不再孤立了。由于朱月明同志的帮助,我在离单位不到一百米的胶州路和新闸路口,分到了一间7平方米的亭子间。小房问只有一个朝北的小窗,冬天很冷,夏天很热,进门后,最大的活动地方就是一张四尺半宽的床。这里是我的第一个家,它是我和孩子两人的家。
1969年6月底,在中国科学院遥感所工作的弟弟守邕出差到上海,顺便看我。他来后的第二天,6月28日,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下午4点多钟,我正在实验室里工作,突然感到从肚子里流出了很多水。黄妈妈(一位同事的母亲)喊了起来: “快上医院,孩子要生了。”弟弟和同事们叫了一部人力车把我送到了离单位不N3里路的静安医院。门诊医生一边把我抬上能推动的转运床,一边瞪着眼睛用上海话对我说:“那能不早点来。侬做小人姆妈,要对伊负责,好好架悃叻嗨。”房里连我共4人,一位姓陈的中学老师告诉我,这里是待产房,等到产门开后才会被转到产房里去。我向四周看了_下,这里的每个产妇身旁最少都有两个人陪着,大都是丈夫和母亲,唯独我是自己一人。弟弟去打电话给朱月明同志,他还要打电报给我在北京大学工作的丈夫,让他请假尽早赶来。
待产房里疼痛的喊叫声,随之而来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安慰语言和音调此起彼伏,接踵而至,实在令我涕笑皆非、意外之极。顷刻间,这乱糟糟的情况静了下来,原来是五六个人跟在一位年近50看上去很稳重、很有经验的女医生来查房了。她是产科主任,是这里的最高权威,自然所有人都希望能得到她的关心。她按顺序一一询问、听诊,给带来的人讲解些事情,也回答产妇或家属的提问。查到我时,第一个问题是你怎么没有人陪同;第二个问题是,你这样安静,是不是没有特别感觉。我告诉她:自己丈夫在北京,想喊也没人听,不如静养。我担心,肚子里的水流完后才到医院来的,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健康。不知道是缘分还偏爱,她对我的检查特别细心。她告诉我说,一切都很正常,不必担心,我会在午夜前后临盆。她要大家向我学习,不要把精力耗费在不必要的大喊大叫中。
晚上7点多,朱月明来看我,她给我做了一大碗鸡汤面,里面还有荷包蛋,要我在不难过时吃下去。她劝我别怕,没有闯不过的关。她那长辈、母亲般的关心在后来的三四十年里一直陪伴我克服一个个困难。这天晚上,我尝试了做母亲的艰辛,虽然克制了在痛苦时的叫喊,却无法抑制自己不时地盼望午夜的来临,渴望尽早结束这艰难的历程的思绪。然而,这个历程带给我的并不仅是痛苦和艰辛,还有一种无法表达的愉快和享受,原来这个历程是在愉快和兴奋的高潮中结束的。此时是孩子出世的那一刻,也是他以第一声呐喊宣告他到来的那一刻,那是1969年6月30日,凌晨1点30分。接生的医务人员,把孩子的两腿分开,用上海话说,“伊拉是弟弟”,她们怕我不懂又说了一遍,“侬格小人是弟弟”。那天在这医院里出生的只有他一个男孩。洗完澡后,护士给他的手上带了一个小圆牌,上面写的是52床之子,3200克和出生时间。她们把他包成一个蜡烛包,包上也有一个同样的小牌,让我看过后就推到婴儿室去了。我要等到取出胎盘处理好伤口后,才能回到病房,我很快就在疲倦和兴奋中入睡了。
第二天的感觉是虚弱、脚下无力、行动不方便。邻床陈老师的母亲,是一位很能干、很慈祥,也很富态的上海老太太。看到我在上海孤身一人,只能吃医院里的饭。她就分了一碗沙锅炖好的红枣、桂园、冰糖、鸡蛋汤要我吃。看着陈老师母女和她丈夫真诚的目光,我很高兴也很感激地接受了这一份盛情。我知道自己领受的是前辈母亲对当代母亲的关爱,是中国伦理道德的表现,这是一份无价之情。老人家还特地提醒我,说给孩子喂奶之前,要先喂他吃点黄连,以免长热疖头的。这样,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吃了那苦不堪言的中药,孩子们奇怪的表情说明他们并不喜欢这种药品。当他们吃奶的时候,都变成一副急不可待的样予,两只小手紧抱着妈妈的乳房不放,吃到喘不过气来才肯停一下。我敢说那是每个母亲百看不厌的镜头。
在医院,我想得最多的是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我喜欢陶渊明“木欣欣以向荣”的诗句。想到北大校园里的银杏、美国加州的红杉、黄山的迎客松等等,我的孩子,一个男孩子应该欣欣向荣,长成参天大树,有顶天立地的气魄。欣欣是他的小名,等他长大我要教他读陶渊明的这首诗,我要他理解“知来者之可追”、“觉今是而非”等人生哲理。在给他起大名时,我期望他能成为一个敢征腐恶的天兵,朱征是他的大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