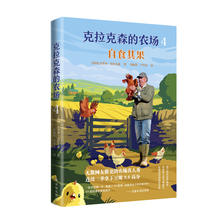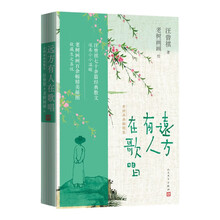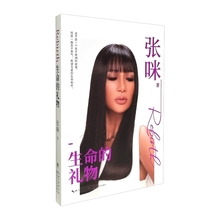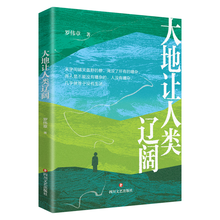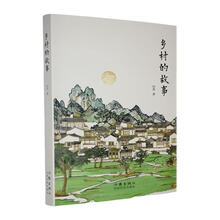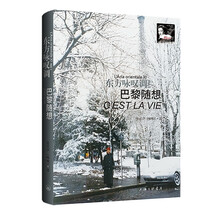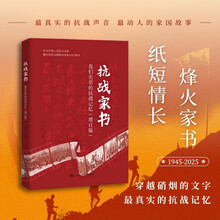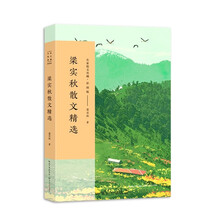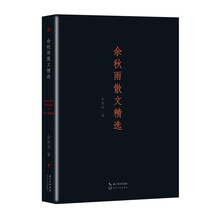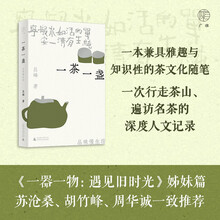在文以明道的大范式中,讲究散文的艺术性主要体现为讲究散文表达的言语技巧,更为注重散文文本的艺术性,追求优美的言辞,强调话语形式的技巧。这类范式可以在不同的向度上使大散文艺术化,通过艺术使得大散文的一些篇目成为“艺术品”“审美对象”。如上所述,《老子》、《庄子》一类对最高抽象意蕴的形上之道的言说往往不得不使用非常规的话语方式,由此发展极为独特的语言技巧。。即使是将文以明道的“道”下降为某种意识形态观念、政治意图,由此建构的散文范式也是需要艺术性的,其最常见的就是散文的诗情画意化、结构的精巧、语词的反复推敲。作为政治传声筒的“散文”不一定就是没有技巧的散文,只是其艺术性往往是限止于技巧性而已。只是由于这些散文表达了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当人们拒绝这些意识形态观念时,也就连带着否定这些散文的艺术性了。
在一些特殊的时代,人的思想探索受到限制,或人们普遍接受同一种既定的思想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追求独立的思想;同时人的个性表现也受到规范,个体的价值被集体的价值同化,或个体被要求为某个理念献身;个人被要求绝对服从领袖或帝王或“组织”;个人的情感活动也被要求具有集体化的情感倾向,要在现实中培养共同的、高尚的感情。因此,散文作家对生存的独特探索、思考不能自由表达,不能公开抒发个性化(有癖好、有缺点、不完美)的感情,于是作家的创造性只能在“文”的层面上表现出来,在这样的时代,散文的艺术性(实为技巧性)、散文的诗化倒得到突出的发展。如武周时期的李峤、崔融等讨好武则天的文章就十分讲究“艺术性”,刘肃《大唐新语·文章》说他们的文章“皆如良金美玉”,由此可见其在技巧上的考究程度。崔融甚至为文章的“艺术性”而献身,“撰《武后哀册》最高丽,绝笔而死。”(《新唐书·崔融传》)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