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1911-1991)他与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并称为当代瑞士德语文学的双子星座。1948年他拜见前来瑞士访问的布莱希特,深受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影响。1960—1965年侨居意大利罗马,后回瑞士定居。1954—1964的十年是弗里施创作的颠峰,他的两部代表作《比得曼和纵火犯》与《安道尔》就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为他带来了世界性的荣誉,并先后获得过许多文学奖,包括德国文学最高奖“毕希纳文学奖”。长篇小说《能干的法贝尔》(1957)的译本达二十四种文字之多。
弗里施代表剧作有:《他们又在唱了》(1945)、《中国长城》(1947)、《战争结束的时候》(1949)、《毕德尔曼和纵火犯们》(1958)和《安多拉》(1961)等;代表小说有:《施蒂勒》(1954)、《能干的法贝尔》、《我就用甘腾拜因这个名字吧》(1964)、《蒙陶克》(1975)和《人类出现在新生世》(1979)等。无论他的剧作还是小说都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危机问题。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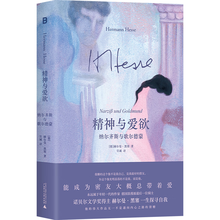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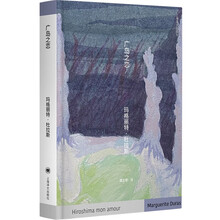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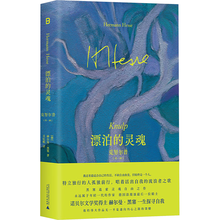





——麦克·罗杰斯《图书馆学刊》
小说展现了二战后的悲惨境遇,字里行间蕴含的多重意义呼之欲出——然后施蒂勒现身说法了:他的叙述狡狯、婉转而又精彩纷呈,像爱伦·坡笔下的凶手,或者雷蒙德·钱德勒小说里的侦探……当施蒂勒的人生谢幕时,结局是令人惊惧的——人类的精神世界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中。
——《纽约时报》
读者无法不把这部作品看成战后最重要的小说之一。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