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不哭
她才一岁半,父亲把她一个人,丢在医院。
麻醉过后。光亮一点点从她的眼睛里消失,熄灭了。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在慢慢合上之后,缓缓地,从眼角落下。
病房很大,静静的。一个小不点,孤零零地躺着,床显得特别大。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就是那个受伤的,一岁半的女孩。她张了张嘴,想哭,脸上挂着泪。她的父亲送她到医院,就走了,不再出现。留下她一个人,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
她的一条腿缠着绷带,悬空吊在架子上,架子很高。她全身都裹了绷带。她这样躺着已经一个月,身边没有亲人。
“42%的面积被烧伤,35%是三度重伤。”主治医生说。
女孩哭起来。
护士摸摸她的手:“宝宝不哭。”
医生说:“宝宝不哭。”
我也说:“宝宝不哭。”
孩子哭得更厉害,喊:“妈妈,妈妈。”
妈妈不在。没有人知道,她还能不能见到她的妈妈,她的爸爸。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的家人是谁。她一个人,被丢在医院。南京红十字医院。
2004年3月9日。白下路,南京红十字医院。
晚上8点,7病区,烧伤科。门卫打来电话:一个小女孩烧伤,很重。护士赶忙下楼,去接。
“我到一楼电梯口,两个男的,前面那人手里抱着个孩子。用棉被严严实实地裹着。上了电梯,他说两天前火烫的。小孩她妈妈回四川老家弄钱了。他在镇江打工。孩子在句容医院治过。医生让转来这里。那人后面跟着的是他朋友。”护士说。
病区处置室。乔骋医生已经在这里等,他是烧伤科主任。“烧得非常重,非常危险。左侧下肢已经炭化。用手敲,硬梆梆的。血管也烧焦了,血管就像树枝形状,僵化凝固着。孩子休克了。”
“孩子上肢全是针眼,没法打针。包扎也很专业,显然在医院抢救过。”
病区进入紧张状态。
“切静脉。输蛋白血浆、输抗生素、输抗休克药物、输维生素。”
“全身检查。换药,重新包扎。”
孩子的父亲靠着床,蹲在地上,用手按着胸口。他的朋友去办住院手续。“我身上只有1000元,孩子她妈妈明天就来,带钱来。”办完住院手续,他的朋友说妻子也在住院,得走。孩子的父亲守着孩子。他站不住,他说三天没吃饭了,也没睡觉。他蹲着。
一个小时过去,孩子从处置室被推进重症监护病房。
孩子在输液。父亲在床边看着孩子。孩子又黑又瘦,脸上皴得厉害,或许是哭的原因,皴的地方甚至结了痂。
父亲摸着孩子的手、孩子的头,孩子昏睡着。他趴在孩子的床边,看她的脸。他两眼充血。
父亲在孩子的床边趴了40分钟,孩子始终睡着。
“我要吃点东西。”父亲一脸痛苦,只在登记表上写了孩子的名字:李霞,年龄:一岁半。家庭地址:四川内江。就捂着胸口,要下楼吃饭。
父亲走了。从五楼的楼梯走下去。
有护士下楼去,在三楼楼梯口看到他。他趴在栏杆上吐,吐完了,一直趴着。
他的表情痛苦而伤心。
他没有来。他再也没有出现。他把自己的孩子,一个人,留在医院。
“孩子处于休克期。四肢发冷,血压低,心率快,发烧,39℃。”乔骋主任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一天、 两天、三天,孩子的情况在慢慢好转,孩子的家人杳无音信。
“3月12日,上午8点。我们给孩子进行第一次手术。”
手术必须尽快进行。孩子左下肢被火烧坏的部分深达两厘米:皮肤——皮下组织——浅筋膜——脂肪,只有深筋膜、肌肉、骨头未曾伤及。
“坏死组织是病灶,是细菌繁殖的土壤。休克期过了,要立即动手术去除坏死组织。”
3月12日的第一次手术是对左下肢进行切痂——清除坏死组织,然后敷上生物敷料。3月15日进行植皮手术。从孩子的头上取下7%的皮,植在她的左下肢。
3月23日,对右下肢进行切痂。
3月28日,对右下肢进行植皮。
“手术都很成功。”乔骋主任微笑着说。
孩子的家人一直没有出现。
孩子不会说话,只会喊“爸爸、妈妈”。偶尔喊一声,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或者哭泣。不笑。不知道是因为痛苦,还是因为对于陌生人的恐惧。
没有人知道孩子到底是怎样烧伤的。孩子父亲当时的描述是,妈妈不在,他们住在二楼,他上厕所。发现起火了,跑进来,孩子就烧成这样。他没有带病历,说全部忘在了出租车上。他除了登记的那点点不知真假的信息,没有留下任何资料。
“他的说法太简单,对于起火的原因,被烧的当时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从孩子的伤情来看,火源在她的左下侧。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孩子被烧得如此之重,至少被烧了有四五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孩子为什么没跑,为什么没人救她?孩子一个人在上面,怎么会燃起这样的火?”
由于忙于抢救孩子,没有人想到仔细盘问。当时火灾情形只能猜测,无法证实。知道内情的孩子的家人竟然从此全无音信。孩子在遭受火烧之后,又失去了最亲的人。
“我喜欢女孩。”他的父亲曾这样对护士讲。
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而他所喜欢的女儿,一个一岁半的孩子,独自承受着身体的痛苦,无助地在痛苦中喊着“妈妈”。
医生、护士,完全打乱了自己的工作规律。她们要给孩子买牛奶、买“小馒头”、买尿片,甚至小玩具。她们要给孩子喂奶、把大便小便,她们要明白孩子的哭,是因为疼痛、饥饿还是恐惧。
“我们3个人,24小时轮流值班。”烧伤科人力紧张,可是孩子现在成了中心。
4月6日下午,我站在孩子的床头。孩子紧张地看着我,眼睛圆圆大大的,惊恐不安。给她东西,她的手一动不动。只是惊恐地看着,嘴一扁,哭出声来。护士给她喂小馒头,她噙着泪,停止哭泣,眼睛还是紧张地看着病床边的不速之客。
她已经是个漂亮的女孩了。“跟刚来的时候不能比。”护士说,“她会笑了,昨天笑了一次。”
总有病友来看她。吊着手臂的、驻着拐杖的。他们静悄悄地站在她的床头,看一会儿,再悄悄地离去。他们在过道中叹息。
乔医生又来看她。孩子哭起来。“她怕我。”乔医生说,“给她换药。每次总是十二万分的小心,用消毒水把纱布沾湿了再揭,肯定还是会疼。”
孩子大声地哭。隔壁病房的一个小伙子,拿了自己的随身听,放在孩子的床头。音乐缓缓飘动,孩子奇妙地安静下来,眼睛盯着。音乐响着,孩子的眼睛渐渐蒙胧。睡着了的孩子,不知道梦里能不能见到她的妈妈,她的爸爸。
“明天还要动手术。”乔医生说。
4月7日,8点。住院医生、护士,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孩子的床边。今天,是孩子的第五次手术。“手术成功,这就是最后一次手术了。”乔骋主任说。
孩子身上被烧坏的,没有植皮的地方这次全要补好。
住院医生剃去孩子头上的头发,用刀刮成光头。手术中要从这里取头皮,植到她的身上。“头部血供好,头皮再生快。另外,以后头发长出后,完全看不出伤痕。她是个女孩。”医生说。
女孩哭了,轻轻地。她也许知道会发生什么,也许不知道。她都会哭。
8点36分。护士把孩子推进电梯。手术室在7楼。3号手术室。
孩子被送进手术室。围着孩子的只有医生,还有我。家属等待区的走廊里空空荡荡。
一个夹子夹住孩子细小的手指,监视器接通。很普通的夹子显得很大,不知道孩子的手指会不会很疼。
心率正常,血氧饱和度正常,血压正常。
“给氧。”护士给孩子接上氧气管。
“麻醉。”麻醉主任给孩子实施全身麻醉。
两位担任助手的住院医生拆开孩子身上的绷带,开始对创面用碘伏清毒。一定很疼。
医生轻轻拨弄着金属器械,碰撞的声音让我的心一阵阵发紧。我盯着孩子的眼睛。亮光在她的眼睛里慢慢地消失,像渐渐地小了并终于熄灭的油灯的火苗。她的眼睛完全失去了光亮,眼角噙着泪,无声地望着天花板。
“孩子睡着了吗?”我问。
“不是睡着了,是麻醉了。”
孩子的眼睛慢慢地合上,手术要开始了。
手术室充满监视器发出的孩子的心跳声。怦、怦、怦、怦,声音不大,可是非常有力,非常稳定。每分钟145下。
9点50分。孩子身上的伤口清理完毕。血袋里的血一滴一滴地滴进孩子的体内。“为了防止失血过多。昨天夜里已经输了75毫升的血,现在还要输225毫升。”乔主任说,“孩子太小,身上血量少。”
10点10分,乔主任开始在孩子头上取皮。怦、怦、怦、怦,脉搏正常。孩子安静地熟睡着,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知道。我退出手术室。她只是一个一岁半的孩子,这个孩子现在正遭受的一切,我不敢面对。穿着无菌的白色大褂,我突兀地站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
孩子在7楼手术室。5楼,她的病房里空空荡荡。病床上洁白的床单铺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一个布娃娃放在枕头旁边。那只随身听悄悄地,摆放在床头柜上。
12点30分。从孩子被推进手术室到现在,已近4个小时。
乔骋主任开门出来:“手术顺利。”
4月8日。
护士给孩子喂着稀饭。“她能吃不少。”护士小姐给我看她手中的杯子。孩子看着我,眼神鲜亮。
孩子的腿还是用绷带吊在支架上,两只手也用带子拴着,怕她乱抓。她的头可以动,眼睛可以四处张望。
“再过一个月,就可以出院了。”乔主任说。
乔主任所说的出院,是指通常意义上,有家的人。
没有人知道,一个月后,等待这个孩子的是什么。
她父亲留下的唯一线索便是孩子曾在句容人民医院治过。可是经过调查,句容医院没有收治过这样的幼儿。
她无处可去。
“孩子出院后,要护理,要帮她锻炼。路还很长。”
“以后,她能走。她的手没有问题,她的智力不会受影响。她能自食其力。”
“但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
从乔主任办公室出来,我再去看孩子。
“她一直喊着妈妈,喊个不停。现在睡了。”护士说。
孩子睡了,脸贴着布娃娃的脸。护士用湿纱布擦去她脸上的泪痕。
“她还要经历很多痛苦。每年都要做一次手术,直到发肓成熟。”医生说。
她才一岁半。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经历,因为采访对象已经走进我的内心,影响着我,牵扯着我。我是一个幸福的4岁女孩的父亲,我为另一个陌生的不幸宝宝而痛苦,她的痛苦我甚至感同身受。因为这,我想替她,感谢这些善良的人们,并且记下他们的名字——虽然,也许他们并不需要:南京红十字医院烧伤科的乔骋主任,是他给孩子带来新生、医院工会郭明主席,是他的奔波呼喊,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孩子;还有烧伤科医生:杨永胜、陈勇;护士:王燕,丁小燕、田亮、梁凌虹、仝开棉、兰志红,她们是真正的天使,是她们把孩子从噩梦中牵引到温馨的人间。感谢的名单中还应列上没有留下全名的钟小姐,她为孩子带来了第一笔捐款。还有小李霞的病友们,他们给了孩子最贴近的温暖。这个感谢名单很不完整,因为只要用心去关注孩子的,哪怕为孩子的命运有过一声叹息的善良的人们,都体现着人性的美好。
最后,我想对孩子的爸爸妈妈说一句:孩子她想你们。痛苦时,她呼喊着你们,恐惧、饥饿时她喊着你们,她在梦中喊你们,在无助孤单时,她要你们。在她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年半的时间里,她最亲的是你们,她最可以依靠的是你们。最疼她的,也是你们。
也许,你们有着自己的无奈,也许,你们有着太多不得已的理由。可是谁都没有权利让一个无辜的宝宝永远哭泣。请你们给孩子一个未来,不要让一岁半的孩子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永远找不到爸爸、妈妈。
她想回家。
(经过多方努力,两年之后,孩子终于被一个合适的家庭收养。她家的附近,就有一座大型医院。)
孤儿院
天亮了,打开门,一个孩子被用绳子拴在孤儿院外面的栅栏上。孩子裹着棉衣,也许是哭累了,躺在泥地上已经睡着。一脸的泪。
2006年9月19日。
在安徽颍上到阜阳的102省道110公里处,一面旗子,高高地插在树桠里。没有风,旗子贴着树干一动不动。一位瘦小的老人在旗子的下面,努力朝远方张望着。
他说,我就是王家玉孤儿学校的老师。
“孤儿院在河的对岸。”他用手指指。
一群母鸡在学校门口的草垛下面刨食,对于来人毫不惊慌。两个七八岁的女孩子笑着喊着,奔过来,打开院子的栅栏门。接着有更多的孩子涌过来,朝我们拍手,笑着,喊“欢迎”“欢迎”。
推开校长室的门,木头门发出吱呀的怪叫。一位老人闻声从墙角的行军床上艰难地爬起身。
他说,是的,我是王家玉。上楼梯的时候,这位67岁的老人摔了一跤,腰部骨折,已经卧床两个多月。
老人从昏暗的角落里走到透着阳光的窗户跟前,笑着,笑容落寞而沉重。孩子们的小脑袋在窗口挨挨挤挤,不一会儿,上课的铃声响起。一哄而散。
这个简陋甚而寒伧的校园里,生活着214个孤儿。
孩子们在上课。
一年级的课桌是一块块的木板,铺在水泥墩上。孩子们看到了我,齐声地,把拼音读得格外的响亮。
秋日的傍晚,风里已经透着阵阵的寒意。高声读着拼音的六七岁的孩子们,绝大多数还穿着拖鞋和凉鞋。
一年级教室的后面,是聋哑孩子的教室。孩子们在画画。墙上贴着几张画好的水彩,美得让人心痛。因为他们之中,已经有人被扬州选去当了玉雕工人。孩子们更加的刻苦,他们有了希望。
而在后面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面,三位老人手里抱着,车里推着五六个几个月大的孩子。都是残疾孩子。
老人们是放弃了家里的劳动,来这里帮忙的。
“想到这些孩子,我就忍不住眼泪。我在家里什么也干不了,我天天来带他们。”
他们都是孤儿。214个孤儿。他们,每一个都有着言说不尽,甚至无法言说的可悲身世。然而,他们看上去,几乎是快乐的。他们的笑容热情而腼腆,他们的眼神单纯而清澈。也许,在经历了太多灾难的之后,衣食无忧,就是他们心目中幸福的全部含义。
孤儿们人生当中的这个小小绿岛,是从王家玉的一次街头偶然开始的。
1994年。
“我到颍上县城去办事,五六岁的一个孩子,在垃圾堆里扒东西。办完事回来,他还在那里扒。我说,孩子,这里东西脏,不能吃。我买了两个烧饼给他。后来,几次来县城,都遇见他。就每次给他买两个烧饼。他一看我,就跑过来。亲热得不得了。我说,算了,你干脆跟我回家吧。”
“他父母都不在了。后来,他大了,送他学了汽修。现在在苏州工作了。”
“他是我收留的第一个孩子。”
谁会在意,在广大的城市乡村,处处都有流浪孩子的栖身处呢?王家玉总是能发现他们,他们也总是对这个面容和善的老爷爷充满不同寻常的信任,这真是难以解释的现象。王家玉亲自发现收留的孤残儿童,在四五年间,竟然有二十来个。安徽阜阳颖上县的这个行为不合常理的农村老汉,一下在四里八乡出了名。出了名的结果,是更多的孩子被送到了这里。到了2003年底,王家玉的孩子,达到了183个。
王家玉出生在贫困县最穷的农家,家徒四壁,少年丧父,三十岁才娶上了患有癫痫的妻子。因为妻子无法料理家务,王家玉远赴东北做伐木工人,竟要背上两个弱智的女儿。能吃苦的他,凭着木工的手艺,开办家具厂,1994年,他的家底有了四、五万,成为当地有名的万元户。到了2003年,他的收入增长到几十万,而孩子增长速度,又远远超过了收入的增长。孩子,让他的厂房,变成了校舍,让他的全家和工人,成了护理员和厨师,更让他本人彻彻底底,从富翁,变成了还有大批欠款的穷汉。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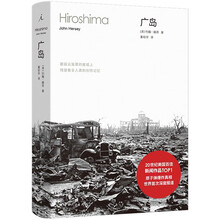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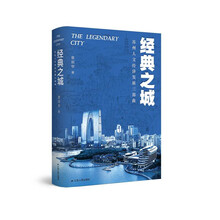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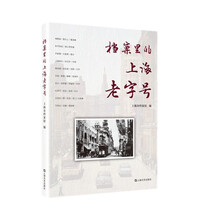
——记《不哭》的作者和设计师朱赢椿与申赋渔
他们认识并不久,闲谈中透露的相似的背景,却让彼此都很放松。朱赢椿,1970年生,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申赋渔,1970年生,颇有名气的记者。人们把这个年龄段还有点出息的人,依然称作为“青年才俊”。都已经顶着这名头几年了,行为作派,不免都有了包裹的成分,“自恃甚高”是才能的人常常脱不了的底色,“相看两不厌”,那就难得了。然而,这两位还真的越来越熟悉了起来,隔个一周,总要聚一聚。眼下,更多聚会是因为某项倾注了两人心血的大作。其实,相聚聊天中太多的惊喜来自于彼此的欣赏和默契,这使两人感到一种纯粹的快乐。
他们之间显然有着太多的相似点:都来自苏北农村;都有着贫寒却自由无比的童年。当小朱赢椿用自然界中所有能找到的颜色:青草的绿、桃花的红、迎春的黄碾碎了,无师自通地创造着儿童的天才的画作时,小申赋渔正四处寻觅着村子里能找到的书,甚至是有字的纸,这些文字被他即兴发挥为更有趣的故事。躺在田埂上的他对着小伙伴发誓:一定会成为文学家。虽然彼时的他们,对何谓“艺术家”“文学家”不甚了了。
后来,他们都进了城,从事着和早年的理想还能搭上点边的工作,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他们都成了村里人教育孩子的榜样时,他们却一直重复着同样的梦魇:他们仿佛一直在做一张永远无法完成的试卷,大片的空白,让他们汗流浃背,心跳过速。他们是折磨人一生的“高考综合症”患者。多年来,高考,成为农村青年人体面地走出家园的唯一通道。虽然朱赢椿成了涉险过关者,申赋渔却被挤下了无望的深渊,但其中的心路历程,同样不堪回首。此后,朱赢椿留校、工作,慢慢洗去了农村少年的青涩,成了很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而申赋渔,则做过木匠、搬运工、书店管理员、公司职员等职业之后,最终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边打工,边学习,完成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学业。
看似各不相干的人生,却在他们的内心,深藏着一样的悲悯与责任。
因此,当申赋渔第一次跟朱赢椿说起进入这个大千世界的一些人和一些事时,久在象牙塔之中的朱赢椿竟然也同样感到了深入骨髓的疼痛:这是另一种真实存在的现实,离他们曾经生活的环境并不遥远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一群遭遇不幸、却经历各异的孩子:因为家庭贫困,一岁半的孩子烫伤后,竟被父亲忍痛遗弃在医院;母亲吸毒被拘,3岁的孩子竟活活饿死在家中;当一个12岁的孩子溺水挣扎时,相距不过10多米远的钓鱼者,竟能心平气和地继续等着鱼儿上钩;渴望回家探望患病母亲的高校学子,竟因无钱购买几十元的车票,他骑上单车,踏上55个小时的归乡旅程。和申赋渔一样,朱赢椿对这些年轻生命的痛苦,感同身受,颇有几分书生气的他,却不能判断,是否因为他和申赋渔已经是好朋友,而多了一份格外的热情,他担心如果他过分的热衷会使自己丧失客观的判断力,他也担心读者会不买一本描述苦难和不幸的图书,但书中描绘的故事却让他如此的震惊、疼痛与冲动,他一刻也不能忘记书中苦难情景,不能忘记那些在贫寒和挣扎中需要关怀和援手的人。他把申赋渔的作品带到了大学课堂,读给外表很“潮”很“酷”的孩子们听,教室越来越静,后来,传来了哭声。
回来后,他对申赋渔说:结集出版吧,我会做出最好的设计,书名就叫《不哭》。
几天之后,他背着书稿去了北京,去谈出版、谈发行。他把全部的心血投入到这本书的设计与出版当中。义无反顾,这是一本过于沉重,屡屡被出版社拒绝的书稿。
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读者,你一定能从内容到形式,感受到这是一本“不一样”的书,它充满了挣扎、悲悯与关怀。它倾注了两个来自乡野的创作者浓得化不开的真实情感。它不带丝毫功利,源自于没有结茧的柔软的跃动的心灵深处。
不知道,《不哭》会让一个陌生人感动吗?会让你内心产生同样的激情和爱心吗?会从书店来到你的书架上吗?不知道这本书上是否会很快落满灰尘,朱赢椿和申赋渔只是希望有一天,越来越多的孩子停止哭泣,露出无限灿烂而美好的笑容。
----------------------------------------------------------------------------------------
■设计是为了忘掉设计
——《不哭》的设计
这是一本极为引人注目的书,放在任何一批书里,它都会跳出来,直扑眼帘,让人忍不住就会走过去,拿在手中翻阅。一层薄薄的纱布,从书脊延伸到了封面和封底上,书脊的纱布上贴着一条毛边的牛皮纸,乍一看,像是在装订过程中突然停下来,时间定格、凝固了,让人感到沉郁而伤痛。封面是粗糙的充满质感的纸张,仿佛洗旧了的布,调子怀旧而感伤,沉重而质朴,含着浓浓的悲悯之意。翻开内页,立即听见了纸张的呼吸之声。叹息、沉吟、落泪、悲愤、恸哭,翻开的这一瞬,情绪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一只无形的轻柔的手,牵着你,走进了最最柔软的内心,轻轻地翻动,不自不觉中,你已经泪流满面。
这本名为《不哭》的书,讲述的是18个孩子的生存和教育困境。朱赢椿,这位著名装帧设计师,为设计这本书,花费了将近半年时间。
朱赢椿说,设计这本书,首先是因为它打动了我,让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流泪的我,流下眼泪。这个时代,许多人已在心上裹上了老茧。这是一本能够融化老茧的书。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心血设计它?我其实是希望不用设计它,人们自然就来读它。可是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如果没有设计,原生态地放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人来关注它。这又是一个出版大爆炸的时代,放在书店,很快就会被其它的书籍淹没、覆盖。这在种情况下,必须有人把它凸显出来。让设计,使那些脚步匆匆的人,暂停片刻。当他们开始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就会将设计忘记。这,是我所追求的。
----------------------------------------------------------------------------------------
■《不哭》是部微观社会史
在强烈变化的社会背景之下,相当一部分中国家庭的孩子,他们正面临着他们难以承受的生存困境与教育困境。然而生存着,就必须挣扎。他们中的一部分在挣扎中毁灭着,一部分在挣扎中寻找到希望。
就是在这艰难的行走之中,时代在他们身上打上了或深或浅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开《不哭》这本书,就是翻开了一段隐藏着的然而却震撼人心的社会史。
在《不哭》中,孩子从出生起,便因社会分层,而面临落差巨大的命运。一岁半的孩子被烫伤,因家庭贫困,竟被父亲忍痛遗弃在医院(《宝宝,不哭》)。贫寒的家境,让品学兼优的高三学生难负重荷,竟然突发精神疾病,从高处坠落死亡;而哥哥的死,给了弟弟必须坚强支撑家庭的理由,弟弟多么希望自己能救贫寒的父母于水深火热,却因为没有哥哥那样优秀的成绩,同样面临崩溃(《重负》)。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批外来打工者的孩子,也进入了作者的视线。他们的被剥夺感、自卑感与孤独感,他们的勤勉好学与朴实,修正着社会对他们没来由的成见(《我在城市边上》等)。在《不哭》一书中,贫困给孩子成长打上的阴影,是最显而易见,无可回避的主题。可贵的是,作者还洞察了重负之下,成长着的生命焕发出的夺目光辉。在《乡路带我回家》中,贫困学子李红光,渴望回家探望患病的母亲,竟无钱购买几十元的车票。他骑上单车,踏上归乡的旅程,历经55个小时。李红光没有印象中贫困生的沉默而忧郁,他是憨直朴实的,又是阳光般明朗的,哪怕当同学沉湎于网络或恋爱,而他的业余时间全部在食堂、在图书馆打工中度过,他依然快乐地坚信,没有水晶阶梯的他,依然可以走向人生的巅峰。
贫困、贫富分化的加剧,不管是不是社会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尚未成年的孩子,却都有失公平。然而,《不哭》在表现时却既深入体贴,又客观中允。其实,在任何社会环境中生长的孩子,都或多或少,受到环境的影响,这影响,又都是正负双向的。因此,社会背景下个人的顺应或执着,均是《不哭》刻意表现的内容。
在这部作品集中,我们看到了沉湎于网络,不可自拔,以抢劫银行求得解脱的大学生(《他想坐牢》);有为了争风吃醋,参加群殴,以至下手凶残的暴力少年(《血色少年》);还有因为自私、因为怯懦,因为大人的冷漠,置溺水的同伴不顾,甚至隐瞒同伴溺死消息的一伙孩子(《守口如瓶》)。翻开《不哭》,每每被时代大背景下,个人的迷茫与无助、痛苦与扭曲所震惊。我们看到的,是飞速奔驰的发展的车轮,对人心灵的辗压。面对庞大的复杂的无可名状的社会,作者选择了他独特的表现视角:因为少年的洁白,时代的烙印总是格外浓重;同样因为少年的无辜,少年的烦恼总能格外引发人们对于社会的思考。
与贫困,使少年沉沦,也使另一部分少年奋发一样,多元化的时代,在淹没了一些孩子的同时,也铸造着另一批孩子。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知识的执着(《9月1日》);对生命的热爱(《微笑的女孩》);对理想的追求(《假如人生是一部默片》)。
《不哭》就这样给我们展开了少年真实的群像,表现着他们的命运、心灵与苦痛。而鲜活的生命,又是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关照,因此,成为时代纪录的组成,厚重而深刻。相信这样的读物,不仅是广大青少年认识自身的最佳渠道,也会引起教育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的关注。
《宝宝,不哭》在文体上自成一家,既具备新闻要素,又采用大量文学手法,擅长将冷静的白描与激情的内心表现相结合,兼具情节的引人入胜与思想的独辟蹊径。而真实性与时代感,作为新闻的要素,在篇目中得到最突出的体现。在厌倦了虚饰的年代,它的力量无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