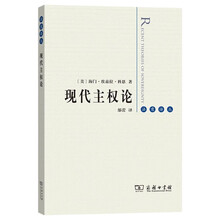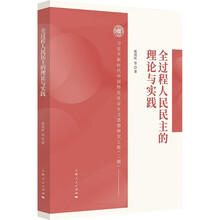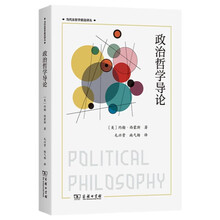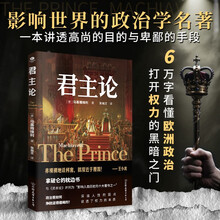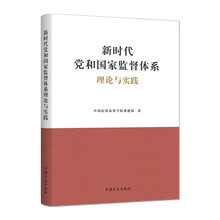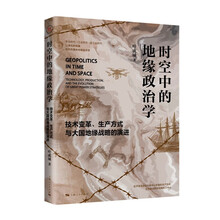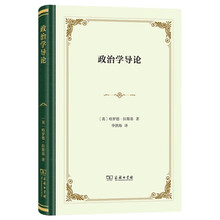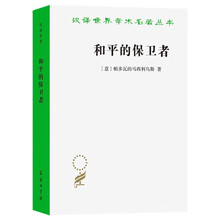第一章 “开端”:康拉德和维柯
“由于个人在政治和经济社会中无力与之抗争而往往保持沉默,从某种角度看,写作是我本人对这种沉默态度的一种反抗。我认为写作不完
全是一种消极的退让行为,因为它代表了某种表述。”①显然,在赛义德看来,写作并不是自说白话,也不是于世无补的纯粹个人行为,它是个人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对抗与对话,是一种具有积极反抗意义的话语实践。
正是基于把写作视为一种具有积极反抗意义的话语实践,赛义德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称为“兴趣期”,即对文学生产的存在问题产生兴趣(all interest in existential problems of literary pro-duction),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思考的时期。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是《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第二个时期是“理论期”。在这一个时期,赛义德广泛接触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各种理论思潮,结合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辨析、思考和整合,并且开始寻找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学术声音。《开端:意图与方法》是赛义德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第三个时期是所谓的“政治期”。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了《东方主义》、《采访伊斯兰》、《巴勒斯坦问题》,并且延续好多年。第四个时期可以称为“美学期”,代表作品为《文化与帝国主义》。在这一阶段,赛义德在学术界的地位已经稳定,影响日益扩大。其学术著作的政治色彩仍然很突出,但已不再处于主导地位。在对美学问题的研究中融入自己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成了赛义德这一时期著作的显著特点①。
从赛义德的自述可以看出,同斯皮瓦克、杰姆逊等当代著名的文化批评家一样,他的学术触角虽然总是伸展到文化研究甚至政治实践等更为广阔的领域,但是文学研究始终是他的整个学术研究的核心和根基。这不仅是因为文学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文学与现实生活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因素更为直接、更为浓厚,也更为集中。而且,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所具有的想象和虚构的特征实际上直接贯穿于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因此以文学为基地,从文学切入文化,在将文学投置于视野开阔的文化语境中的同时,以文学研究中对历史、话语和想象进行关注的视角、方法和理论模型结合文化研究的实际情况考察文化问题,是文化研究中一种既方便可行又十分有效的方法。
赛义德的文学/文化研究开始于他对波兰裔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研究,时间是在“新批评”盛极而衰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