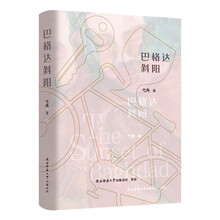第一章 “黑云彩罩住了牛心山,九眼泉打了个闪电。”
1
麦场上发生的一幕,使老顺非常震惊。看到豆垛晃上晃下的时候,老顺以为是牲口偷吃豆秧呢。“呔!”他叫了一声,豆垛就不晃了。老顺四下里转转,也没见个牲口影儿。正疑惑,豆垛又晃了起来。
他便上了场房。
豆垛上,猛子正压个女人晃势,白屁股在晨光中晃得刺目。老顺像挨了一棒。.虽说这个要债鬼曾和双福女人闹出了惊天动地的桃色新闻,但毕竟是耳闻。这眼见,却分明成闷棍了。他仿佛才发现儿子竞也是个男人,也会伏在女人身上干他以前常干的事儿。这使他震惊别扭。听说见了这类场面,会一年不利顺的。老顺倒不在乎这个,他在乎猛子那惊慌中带点儿恼恨的表情,其中蕴含的内容很复杂,既有干了丑事被人发现的尴尬,又有对父亲多管闲事上房嘹望的恼怒。还有啥?破罐子破摔?还是……怨老子没给他娶媳妇?……还有什么?老顺晃晃脑袋,晃得脑中嗡嗡响,却晃不出个清晰眉目。恶心。他只是嘀咕一句。
日头爷在东沙丘上探出个惨白的脑袋。老顺脸上烧烘烘的,嗓子很燥,像年轻时在寡妇门口徘徊时一样。日怪。他有些恨自己了,干丑事的,又不是他,羞啥哩?……也难怪,儿子大咧,到了不规矩的时候了……又不是骟马……便是骟马,见个齐整些的骒牲口也跳哩,没法。没啥……只是,老顺口里虽“没啥”,可心里总觉得有点“啥”呢。而且,那点儿“啥”,总叫他心里怪不舒坦。
这也怪他。
真该怪他。六十岁的人了,咋想到上房呢?可谁又知道儿子正把豆垛当婚床呢?知道的话,躲还来不及呢……问题是,为啥偏……又是上房又是长伸脖子观望呢?说明他发现那晃上晃下的样子不太像牲口吃豆秧的。
只记得那个白晃晃的屁股和猛子那扭曲得变形的脸闷棍似的把他击晕了。他怔了怔,不合时宜地咳了一下,但马上又觉得自己咳得很蠢。他手足无措了,脑中有千万只蜂在嗡嗡。
跳下房时,老顺甚至没经过那截矮墙——那是特意为上下方便而留的,他忘了上下房应有的程序,直接从房上跳到后面的沙堆上。那情景,极像逃脱了枪口的兔子。
“哎呀,老顺,练轻功吗?”孟八爷嬉笑道。
老顺尴尬地笑笑。他偷望孟八爷,发现他并没发现自己失态的原因,遂将提悬的心放下,干咳几声,又窥一眼使他失态的豆垛。豆垛仍静悄悄耸着,没一点儿声响。那两人,肯定“恶心”地凝着,不敢再晃势了。老顺心里骂:不要脸,大天白日的。
孟八爷像往常那样,露出挑逗的捉弄的笑。老顺已习惯了他这老顽童相,但他心虚地发现,对方此刻的笑与以前不大一样,难道他也发现了吗?这可是个笑料啊。他定会这样取笑:“白屁股使老顺成了兔脸扇成抹布了,咋不见亥母来保你?
老顺向来不管那些无聊的话题。前世呀,后世呀,轮回呀,在他眼里都无聊。就“现在”,都活不明白,管啥“过去”,提啥“将来”?塞满老顺心的,仅仅是眼前的事:猛子的媳妇咋生发?灵官究竟在外面搞啥鬼名堂?就这。别的,闲扯淡。
老顺叫过神婆,托了个事儿,叫她好歹给猛子介绍个母的。豆垛上的一幕,鱼刺般卡在嗓里。……这愣头爹爹,再不给拴个母的,怕要反天哩。
忽然,传来毛旦的破锣嗓门:“噢——,出金子了!”
一堆娃儿也叫:“噢——,出金子了。”
老顺想:“真有金子呀?”他晃晃脑袋,随了众人,往白虎关颠去。
3
一月前,双福带了几十个沙娃,来到村里一个叫白虎关的河滩里,掘窝子,扎木笼,说是淘金。
老顺耸耸鼻头说:“想金子,头想成虼蚤大了。若有金子,早叫祖宗挖了,能留到现在?”村里人也不信,都说这沙旮旯,狼都不拉尿,哪会有金子?都笑双福。双福在村里招沙娃,好些人不热心。
活六十年了,老顺还没见过金子呢,只听说是黄的,会发光,很重。此外,实在想不出金子还有啥特点。倒是听祖先说过,沿了白虎关上行,是天梯山;再上行,是磨脐山。磨脐山下有个金磨,老在转,放上石头,也能磨出豆瓣儿金。开这山,得抓山鸟和支山石。听说几辈子前,祖先养过个鸡,疵毛郎当,瘦如病鸦。天梯山的道人说,这便是抓山鸟,叫村人弄些豆子,喂那鸡,说是喂满百日,才可抓山。安顿之后,道人便去找支山石。哪知,喂到九十九日,豆子没了,祖先心急,放开那鸡,鸡便飞向虚空,一下,就抓起了磨脐山。可惜,没那支山石,鸡力尽而死。半个时辰后,道人带回了支山石,山却合拢了,再也无法打开。
这故事,流传几百年了。
老顺想,传说毕竟是传说,只有小孩子,才把传说当真。村里人都等着看双福的笑话呢。谁知,一月过去,他真捣腾出金子了。
水蜿蜒着,从水库那儿,银蛇般游了来,游向涮金槽,将木槽中的沙冲去,槽凹处就留下了一层黄澄澄的砂金。老顺咽口唾沫,晃晃脑袋。他有种做梦的感觉了。这就是金子呀?抬起头,日头爷在嗡嗡地叫。
因猛子和双福女人有过一腿,闹出了天大的风波,老顺竟莫名其妙地反感起双福来。他想:“天是个溜沟子货。这双福,成财神爷的卵子儿福蛋蛋了,又是上电视,又是上报,听说企业还要上市卖股票哩;偏又叫他弄出了金子。村里的穷汉连裤子都穿不囫囵哩。”他愤愤不平了。
大头也闻讯而来,人还在百米外,声音早过来了,“双福,这一宝,还叫你押准了。我还以为你赔定了呢。我算过,光沙娃的工资,就上万了。”双福笑道:“瞎驴碰草垛昨成?我想,既然上游的双龙沟有金子,不定下游的白虎关也有金子。闹个仪器一测,嘿,那电阻,真是金子的。”
老顺不懂啥电阻,却见过揭墓贼用的仪器。听说它会发出电波,能人地几十米,是铜是铁,一看表上的数字就知,想来,双福就用这法儿测的。心里仍噎噎地难受。
双福将沙金倒入茶缸一端了淘金盆,叫沙娃上几锨沙,迎了那水势,一下下涮。沙子咕嘟着,被水冲走了。老顺屏了呼吸,心却随双福的手晃荡,想:“这次,别出金子。”但随着沙子的减少,晶亮的黄色又出现了。
“噢,金子!”毛旦又叫。
老顺恶狠狠说,“金子也是人家的,你叫啥?”
毛旦笑遭:“金子虽是人家的,可是我们挖出的。”老顺啐道:“才当个沙娃,就这样牛气。若是当了县太爷,还有老予们活的路数吗?”毛旦笑道:“我要是当了县太爷,谁不送礼,就杀谁。”又悄声说,“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想叫他败呢。没啥,那娘们也愿意叫猛子操。拔了萝卜,有窝窝儿在呢。”这下,说到了老顺疼处。他脸色大恶,‘啐毛旦一口。毛旦笑嘻嘻望老顺一眼,做个鬼脸,背起柳条筐,下了窝了。
因了猛子那档子事,老顺没到窝子上来过,这时既然来了,就索性开个眼界,见那窝子,直直扎入地面,黑黝黝的。老顺眯了眼,瞅半天,子。嘿,姿势好极了。嘿,老呀老了,还能叫个X吓惊……真没见过个世面,连盘子大个×也没见过,……”噢——,吓惊了。”声音是够难听的,而且不分场合,很叫人头疼。他留意地瞅一眼孟八爷,却放心了。因为他已眯了眼,把目光转向田野里蚂蚁般忙碌的人们。
老顺没有和孟八爷喧谈的兴趣,也想给垛上人一个卸妆的空隙,就梦游似前行。……他不由替儿子着急了。正是上地的时候,人来人往,叫人窥见,脸往哪儿搁?又不能明里提醒儿子加快动作……丢人不如喝凉水,祖宗羞得往供台下跳哩。
要债鬼。
该给娶媳妇了。老顺想,儿子大了。他有些吃惊,儿子仿佛吹气似的。他简直来不及反应,就一个个长成墙头高了,而且……他似乎读懂了儿子方才的表情中叫他难以捉摸的内容,那就是:“谁叫你不给老子娶媳妇呢?老子当然操别人。”真是这样吗?也许是……一肯定是……他想到猛子尴尬和恼怒中透出的那种任杀任剐的蛮横昧道,叹口气。老顺望一眼此刻还静静的豆垛,往村里走。是该娶了。这是羊头上的毛,早晚得燎。只是,手里无刀杀不了人,钱是个硬头货,一个媳妇得几万票老爷,哪儿生发?麦子倒还有些,扎紧喉咙,也能粜个三五千。粜吧。迟早得粜,迟早得娶,原打算防个饥荒年啥的,现在还防啥呢?今日有酒今日醉,管他明天喝凉水。混上一天是两半日子。
一进屋,老顺就躺在炕上。他觉得很疲乏,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乏,乏透了。莹儿带着娃儿站娘家去了,屋里自然清静。老顺懒得睁眼,也懒得去想啥,但猛子恼怒的脸和那个白屁股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晃得心里愈阴沉了。院里的公鸡正追赶母鸡。母鸡的叫声半推半就骚气十足,搅得老顺怒气冲冲。隔着窗子,他品“(口欧)(口欧)”了几声,却喝不断鸡们的浪声浪气。于是,他恶狠狠呸一声,跳下炕,脱只土头土脑的鞋子,扔出去;活活拆散了那对恋鸡。
老伴被大惊小怪的鸡叫声惊出厨房,见老顺一蹦一跳地去捡鞋,嗔道:“鸡又没挡你吃屎的路,你打它干啥哩?”
你才吃屎哩。”老顺拾个小棍儿,刮去粘在鞋上的鸡粪,狠嘟嘟顶了一句。
那只惊魂渐定的公鸡又开始了被破鞋惊断的性骚扰。老顺却懒得再理会,心想,也难怪,公鸡也知道干那事儿,何况人。老顺没心思和老伴说笑,取了烟锅和打火机,“噗——”烟弹划弧,飞出老远。几只鸡扑过去啄。老顺尽量让那烟在肺里多转了几转,牙缝里发出了长长的嘶嘶。老伴见老顺心事重重,问:“究竟咋了?颠个脸,叫人心里乱哄哄的。”
老顺许久不语,一下下咂着。呛人的烟一股股腾起。老伴又问:
“究竟咋了?”老顺恶声恶气地说:“问啥?你那个爹爹大天白日干驴事。”“谁?”“除了你那个愣头爹爹,还有谁?”
“猛子?”老伴一怔,又笑了,“当大的要像个当大的,拿儿子开啥玩笑。”
老顺狠狠咂几口烟,鼻孔里喷两股横气:“我咋不像当大的?这是实话。”
老伴瞪大眼睛,左右望了一下,一脸鬼祟地问:“和谁?”和谁呢?这下,轮到老顺瞪大眼了。谁呢?不知道。他竞把这个关键问题忽略了。这确实很重要。她究竟是谁?是姑娘,还是媳妇?是谈恋爱,还是打野鸡?对象不同,性质就不同。老顺拧眉,死命回忆那场面,好从中捕捉一丝信息,却不料脑中茫然,一片灰白。不要说那女人的影子,连儿子的脸也不知逃何处去了,好容易显现的,只是那个白屁股,而且不清晰,像波晕荡漾的水中的月亮那样恍惚。老顺懊恼地嘿一声。他发现大脑老和他作对,该记的记不住,不该记的,却刻在心上。比如,方才的事,任何一个老子都会恶心,可那一幕却老晃,叫他疹怪怪地极不舒服。而现在,研究案情需要材料,脑中却白茫茫一片了。他懊恼地拍几下脑袋,却想起,那一瞬,没看见女人的脸。
“不知道。”他无奈地说。
“那就是个屁。”老伴说,“谁告诉你的,你就打掉他的狗牙。哼,现在的人,跟个音音儿,念个经经儿,就爱捣闲话。要是我,不打掉他狗牙才怪呢。”
老顺火了,“你打谁的狗牙?来,打老子的。谁说你的活爹爹的闲话?是老子看见的,老子还能红口白牙捣他的闲话……老祸害!”老伴叫煮山芋噎住似的瞪了眼,脸上的肉蹦蹦跳着。许久,话音才冲开闸门:“看见了就看见了!凶啥?成精了?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还有脸说儿子……”
老顺脸上白一阵黑一阵,鼻孔里开始有了横气。初时他还在忍,等她提起箩儿斗动弹,开始涉及他早年的隐私时,便忍无可忍了。他伸出左手,撕住老伴的头发,抡圆右掌,瞄准那张黄脸,狠狠扇了几下。老伴哭叫起来,边哭边骂,内容愈加难听。老顺很懂得速战速决的游击战术,数招得手,马上抽身,顺手还拿上了动手前放在窗台上的烟锅子。
2
庄门外凉飕飕的漠风一吹,老顺的头脑清醒了,气也消了。这是几十年常做的功课。动口是老伴的能为,动手是老顺的强项。照例是老伴先占上风,老顺要后发制人结束战争,前者再用哭声打扫战场。此后,老伴要耍几日威风一日不可太过分——老顺嬉皮笑脸赔小心。而后,万事大吉。他们的刚柔对垒向来是和谐的。精明的老伴即使在耍威风时,也忘不了打量笑嘻嘻的老头子是不是突然咬起了牙。“老啊老了,咋又是刀枪矛子的?”老顺晃晃脑袋。他有些后悔方才的手重。大儿子憨头一死,老婆子真皮包骨头了。小儿子灵官去了外面,又不来个音声儿。老婆子老念叨。念叨归念叨,可人家不通个声气儿,你有啥法子?娘老子的心在儿女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无义种。
真吃枪药了。老顺想,按说,也没啥大不了的事,叫人家说了说两句,动啥手呢?……可没治,许多时候,人由不了自己,手也由不了自己,心更由不了自己。心要使气,手要出气,老顺有啥法子?他想笑,可口一张,却叹了一口气。
想到老伴挨揍的原委,老顺的心一下子暗了,眼前又出现猛子羞恼的脸。这时,他才真正确认了那是“羞恼”。记得,在双福捉奸的那夜,猛子就朝他吼过:“谁叫你不给老子娶?”要债鬼。
老顺终于明白了老先人为啥叫儿子“要债鬼”。确实,儿子是啥?所谓儿子,就是能理直气壮地从你兜里掏钱,从你碗里抢肉,从你口里夺食,而又心安理得的那个人。莫非,真是我前世欠了他们的债?像大儿子憨头,从老鼠大,抓养到墙头高,娶了媳妇,生了病,债要完了,腿一伸,走了。走了就走了,还落了一屁股的债,叫老子背。不是要债鬼是啥?
现在,又该着猛子要债了。一想到猛子裸着身子在豆垛上晃势,老顺心里又毛呵呵了,就往人多处走。这是他惯用的法儿,烦了,就聆听杂音,去淹那烦。
近来最热闹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金刚亥母洞,一处是白虎关。前者是村里人挖土山时发现的,洞里有好些文书和文物。村里人加固了洞窟,宗教局下了批文,就变成了道场。后来,双福出钱引来了电,又将凉州城拆了的十多间老房子搬到洞外。村里人爱新鲜,闲了,就来这儿。
此刻,洞口正围了一圈人。老顺听出,仍在喧王母娘娘。这是个新话题。说是某一日,村里来个老婆儿,留下一封信,人说那是王母娘娘——就是玉皇爷的大老婆,她得知人间有包天的灾殃,才私下天庭,拯救世人。信上说,当今世人不善,恶人横行,不信神,不敬佛,上欺天,下欺心。上天震怒了,要降下罪来。到那时,日不出,月不明,洪水浸天,毒虫遍地,瘟疫四起,白骨盈野,猛兽横行,人食同类,有房无人住,有衣无人穿,有地无人种,有粮无人吃……好个可怕!喧谈者你一句,我一句,都说末日到了。语气倒兴奋得像叫驴,仿佛既怕末日,又希望它快些来到。都说,怪倒是怪,那次的黑风,像原子弹爆炸一样,一下子就把天吞了。太阳呀,世界呀,全溜进它肚里了,少见。……按神婆的话说,世界到眼皮底下了。
“这就叫劫。”齐神婆说,“在劫难逃呢。过了青阳劫,过了红阳劫,挨上白阳劫了。谁也得过那个道儿。”一个问:“劫是啥?”齐神婆道:“劫就是劫。国家不也承认有劫吗?文革不就是十年浩劫吗?那就是劫。旋风一样,碰上啥,啥就卷进去了,树叶呀,灰尘呀,纸片呀。人也一样。你想躲吗?成哩,得行善积德。”
村里怕末日而修行的人多,老伴的头也信成个蒜锤儿了。可老顺不信,大的理由说不来,但他瞎猫盯个死老鼠,只问两点:一、“老婆子,你不是行善吗?为啥老不干不净地骂我?”二、“老婆子,金刚亥母不是保你吗?我扇你耳光时,她干啥去了?”这样一问,老伴就大眼瞪小眼了,吭哧半天,便涨红了脸,用撒泼来代替说理。老顺呢,就嘿嘿笑了,骂她“狗咬火车,不懂科学”。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