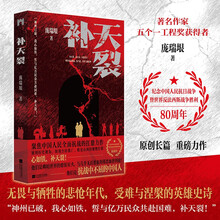晋阳宫内婆娑的柳丝间鼓噪的声声蝉唱,在丝竹的声韵里,显然苍白了。身着方心曲领回纥装束的宫女,在悠扬的长笛、齐鼓、琵琶、笙箫中跳着回纥舞。这是鼎盛时期的大业惯见的一种宫廷舞蹈。穿行在迂廊的晋阳宫监裴寂,没有胆量享受晋阳宫的乐舞,把美丽的春色献给了晋阳的主官李渊。
沉醉在花丛中的李渊,不知道这些身穿回纥粉裙的宫女,叫什么名字,也从来不问她们叫什么名字。这个掌控陇右十三郡兵马的封疆大吏,不过是一只偷食晋阳宫脂粉的硕鼠。在虚妄的缱绻里,在浮躁和惶恐里,期望着遥远的梦想。他耐心地等待时机,又在到来的时机跟前如履薄冰。他渴望永远拥有晋阳宫的春天,他知道只有皇权拥才有这样的艳阳天。他不期望世事只成就他是一个脂粉英雄,那觊觎中的皇权,已经在他的梦想里,越来越清晰了。
晋阳宫的宁静和祥和,散去了他的浮躁和那些理还乱的思绪。在春天的轻音中,暂停了他徘徊在梦想边缘的脚步。那些舞蹈中的粉裙,在松散中春光乍泄,带着如兰的气息。妩媚和嬉笑,围绕着缠绕着,李渊在迷乱的粉裙里,熏染欲醉。他渴望皇权,也渴望无限春光。在遥远的扬州,逃进春光去的杨广,也有着他这样享受春光的平和心境吗?或许在江山和美女之前,他和那位表兄一样,掂量不出孰轻孰重了。
裴寂在门脸儿窥视一眼,叫了一声唐公。李渊在缤纷的粉裙里,侧头瞧一眼笑了。他没有松开环抱酥胸的右手,只腾出左手儿,冲宫门脸儿的裴寂一扬。踱进宫来的裴寂,在乐舞声中张大嘴巴说:“刘武周谋杀了王仁恭,在马邑易帜了。”
“您说什么呵?”李渊仿佛没有听清楚。
“刘武周兵变,谋杀了马邑太守王仁恭。”裴寂大声说:“刘武周还袭取了汾阳宫,所获宫女悉数献给了始毕可汗。”
李渊一声叹息说:“不知道是一件好事,还是坏消息?王仁恭一世英名,断送在这样一个小人手里了。”裴寂说:“王仁恭是唐公的劲敌,当然是一件好事。刘武周投靠了突厥人,和王仁恭相比,收拾起来容易多了。以他的才能,绝不是与唐公最后角逐天下的人。”李渊笑说:“刘武周不过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没有煮酒论英雄的资格。有突厥人做后台,打狗就要看主人了。”
裴寂困惑半天,小心翼翼地问:“唐公的意思是……”李渊犹豫地笑说:“等等再议吧。”裴寂会意地笑了,又说:“唐公,二公子和刘文静在留守府等您议事呢。”李渊无奈地说:“连这晋阳宫的清静,我也守不住了。议来议去还不是老话题嘛。”裴寂说:“怎么是老生常谈呢,唐公已经尽去马邑威胁,此时是起兵的良机。”李渊从花丛中挣脱出来,怏怏出了晋阳宫。
此时远在扬州的表兄杨广,或许有着相同的感受,但他们没有相同的渴望。大隋帝国的社稷,正被无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和兵变者分割。辽阔的大隋,被权欲和武力恣意裂疆,划分势力范围。在混乱中趁势而起的形形色色的英雄,在黎明的前夜,演绎着不同的历史角色。不管众英雄沉浮的结果,李渊势必从名存实亡的隋王朝脱离出来,完成一个封疆大吏到兵变举旗的角色轶变。不管他怎样深谋远虑,那通往巅峰的权力之旅,一样的凶险未卜。世事成英雄,不知逐鹿没落大隋王朝辽阔疆土上的群雄,谁能成为新王朝的主人。
颠晃在官轿里的李渊,没有听到柳笛无序的叫声,那枯燥的蝉唱,令他越发浮躁了。仿佛封闭严实的官轿,把他从大业十三年的春天,隔开去了。从大业九年春天,他这个涿郡督运,与宇文士及浅议兵变谋反后,对风雨飘摇中的大隋皇权,一刻也没有松弛过觊觎,他在等待中攫取到了权力,积蓄了取而代之的资望,耐心等来了易帜的最佳时机。在从容的筹措中,君臣恩义,姨表亲情,全然被权欲吞噬掉了。那逃进温柔乡去的杨广,貌似坚强的背后,脆弱如玉。唯那南国的春燕,呢喃如语,在旋落的宫花里,和着主人伤春的思绪。
易帜只是时间问题,李渊所虞是逐鹿中原的结果。齐郡丞王世充依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瓦岗李密掌握着最强大的一支反隋武装。他这个视世而起的大隋封疆大吏,能够平定群雄统一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王朝吗?他不知道那通往巅峰权力之旅,充满了怎样的凶险。假如他那位极善决断的夫人窦氏不死,或许更能坚定他的自信。然而那来自女人的力量,在大业九年的春天,梦断涿郡。唯有那一摞摞娟秀的诗帖,静静躲在书房的深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