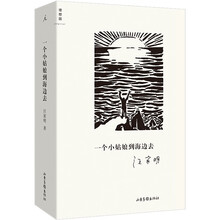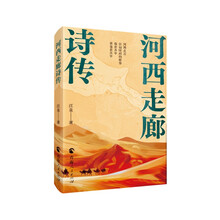小说篇
假钞
(一)
那时节,我还只是县中学里的一名少年。
我所在的班级,叫理工实验班,又唤作少大预科班,顾名思义,是专门培养少年大学生的。(我后来了解到,中国科大、上海交大等几所国内著名大学里都设有专门的少大班,培养一些早慧的神童。)当时不知有多少人打破了头想挤进这个班都没有成功。
因为这个班的名气大,我爸爸也竭力想把我弄到这个班上去,我这个暴发户的儿子刚刚随家从乡下搬到县城里来,脑子里憧憬的是一种野马般的悠闲生活,并不想跑到那种班级里去搞竞争。但我爸爸吃了秤砣铁了心,请了校长喝酒,并当即把包着三块钱的红包给了他。(一块表示一万,一担是一百,这是我们那的说法。)校长仗着酒力,当时在桌子上就拍了板。
进去后一段时间,我就发现,起码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像我一样拉着关系递着票子进来的,另外三分之二的人靠的是真本事,但他们都早已过了少年大学生的年龄,其中有三个人,是为了考这个班而复读了一年初中的。
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我便觉得心安理得了,于是不务正业开始游手好闲起来。我的暴发户爸爸花了三万块钱,挣回了一张短期的脸面。他跟其他暴发户介绍我时说,“小三,我的崽,在少大班读书。”那些肥头大耳,一脑袋煤炭渣子的人就会“哦、哦”几声,脸上露出羡慕的神色,好像一夜之间看到我爸由暴发户变成了真正的贵族。(他一直都是为了取得这种身份而不懈努力的。)
也不是没有考上少大班的,上一届就有一个,考上了上海交大。但他虚报了年龄,他压缩自己数年生命后,在年龄一栏里光明正大的写上“13”,于是他金榜题名,去做神童去了。一想到这个胡子拉渣的神童还要在大学里装几年孙子(幼稚),我们就不禁要为他捏几把汗。
课堂上的生活,我每天要么是嚼槟榔,要么是看武侠。要么就是边嚼槟榔边看武侠。教室后面这几排,塞了有十几个我这样的学生。比如王伟业,他爸爸是副县长;江海涛,他家里开了全省数得着的有名气的化肥厂,像我这样的,分量算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这个教室,基本可以分做两部分,前半部分,是认认真真来读书的,后半部分,是专门来混日子的。所以一上课,就响起一片嚼槟榔的声音。对于这种状况,我猜学校领导和老师都是知情的,所以只要我们这群“油子”安分一点点,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的。但过分了也不行。
有一天,我们江海涛同学就头脑发热了,他觉得嚼槟榔这种运动乏味了,就和他的同桌下起了象棋。当然,他们还没有下盲棋的本事,就把课本垒起来当盾牌,在桌子上排兵布阵。可是他们低估了班主任杨老师的侦查能力,他们过于沉静到两人世界里去了,完全没有意识到杨老师已经停止了授课,完全没有意识到杨老师的脸色已经变成了猪肝的颜色,自然,他们没能抵挡住从杨手中怒飞过来的教鞭,没能抵挡住杨急行军似的脚步,也没能阻止他们的课桌从二楼坠落到一楼。
他们的课桌“砰”的一声,像太空飞来两块陨石,砸在书声朗朗的校园,溅起一片“啊、啊”的回响。(惊呼声)
江海涛和他的同桌被不光彩的逐出教室,我们的杨老师表示完她的愤怒后,继续给我们上课,她挺立在讲台上,我们龟缩在座位后。这时,我们听见,她的音色在高音部分竟然变得有些颤动,这时,我们看见,她的眼眶在激情之处竟变得有些潮湿。她、她、她这个八十年代的“三八红旗手”,在那里慷慨激昂,壮怀激烈,她是不是觉得自己又完成了一项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呢?天晓得。
第二天,江海涛同学就组织了反击。一封长长的信件出现在同学们的眼前,信的末尾有几个鲜红的手印。他解释说,这是正义的事业。他说话时也满脸正气,满怀激动,仿佛他站在了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广场,手里拿着的是油印本《天安门诗抄》。对此,我们有些同学表示了犹豫和怀疑,他们的磨磨蹭蹭让江海涛不快了,最后他只得使出撒手锏,拍着一些顽固分子的肩膀说,摁嘛,摁嘛,摁了对你只有好处,这个月的饭票我给包了。
这封长信到达校长办公室以后,我们班就来了一个新的班主任,他姓张,长相特别和蔼可亲,说话也和气。
原来的杨老师,被调到城关中学教初中去了。
这个张老师成天笑咪咪的,肚子里却尽是些馊主意,他一上台就拿我们开刀了。这不,他见“剿匪”不成,改成了“绥靖”政策,把我们的座位秩序打乱,重新排过,美其名曰是“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实际上是想打破我们的联盟,瓦解我们的势力。
这样,和我同桌的王伟业被无奈地调到了前面,同时给我分配下来了一个新同桌,叫刘任重。
(二)
他长得高高瘦瘦,很干净,也很黑,额上皱纹密集深邃,看上去有些未老先衰,像个非洲国家逃难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不带眼镜,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珠总是瞅着天上,走路时也总是昂着头,目光直射过我们的头顶,好像看着后面遥远的地方。所以他虽然看上去是个非洲国家的知识分子,但在表情上却是一个来自欧美的知识分子,高级得好像不得了。
他的长相就跟他的目光一样严峻,语言也像他的身体一样单薄。
是以故,当他分到我的旁边后,我马上回敬了一个高傲的眼神,以表示对他到来的不欢迎。
他照例还是昂着他的头,对我的表态似乎视而不见。他表情严酷,这严酷里还带着一种木讷,他眼睛看着你,脑子里却仿佛在想着别的什么东西。
当我与他交往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他其实也挺和善的,他不说话的时候板着个面孔,话多尤其是兴之所致的时候还是蛮有激情的,只是这样的时候比较少而已。
后来考了一次考试后,我又发现,他和我一样,也是交了钱才进来的,也是一个自费生!因为考试成绩单的“备注”栏里写得清清楚楚。
他考进来时差一分,交了八千块钱。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脑子里愤懑得快要长出两个犄角:他娘的都是交钱进来的,凭什么他可以少交两万二!以为我们家是个土豪劣绅,可以安个名目随意抢浮财呀?
当时我差点就想去找校长动手。后来刘任重的一句话,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说,如果不是学校想招这么多自费生,分数线不会定得这么高,我也用不着多交这八千块钱。他说这话时,牙齿紧咬着下嘴唇,脸上都涨得红了,好像受了天大委屈的正是他,而不是我。
总而言之,我认识了刘任重,而且开始慢慢地了解了他。
他是个读书发奋得想拼命的学生,和我不是一类人。为了表示我对这位新同桌的不满,我利用我那有点小聪明的头脑和大把的业余时间给他想出了个绰号,叫做“麻杆”,盖因其长得消瘦撇长的缘故。他并没有注意到这绰号里蕴含的贬低情绪,我叫“麻杆”,他也乐呵呵的答应。
我说,“麻秆,借作业抄抄!”
“看姑娘去呀,麻秆!”(我们常爬在栏杆上看楼下操场里的女同学。)
或者说,“麻秆,走,撒尿去!”
他多半就答应了。但有时候我叫他一起和我出去吃饭,他就扭扭捏捏起来。
学校搞封闭式管理,中午都在食堂吃饭,食堂伙食能吃的么?白菜煮土豆,不见半点油星!用李逵的话说,叫口里能淡出个鸟来!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