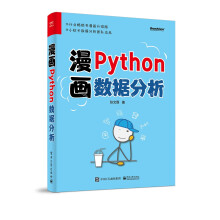耿谆的家与国
九十三岁的耿谆已经很少走出家门,二楼的书房兼客厅,和那问不大的卧室,差不多成了他活动的全部天地。
每天早上,他七点钟起床,此时二儿媳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早饭,通常是菜馍和蛋茶——两种在河南襄城最普通的吃食。吃罢早饭,他开始读书看报写毛笔字。由于视力下降,老人读书看报都要借助放大镜,惟有写字一项,他的精气神却一点不输常人。写字时,他一定要站起来,不仅毛笔在手里握得很稳,而且落笔时笔锋也是丝毫不抖。
“眼神不好,只能写大字,而且写得也比以前少多了,只有别人要字的时候才会写。”耿谆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沓信,“有云南的、浙江的、安徽的、湖北的。”说这话时老人看上去很高兴。自从他的书法作品在《书法报》上刊登以后,求字的信就络绎不绝。老人的字写得好,又是名闻中外的老英雄,自然得到很多书法爱好者的青睐,而耿谆老人也是有求必应,写好后,他会亲自写信封,装好,然后叮嘱自己的孙子耀波尽快给人家寄去。
在河南省襄城县干休所一栋普通的二层住宅里,耿谆老人平静地享受着自己的晚年生活。阳光会透过书桌前的窗户照射在他的脸上,照亮他的白发,照出他脸上的皱纹。
与耿谆的名字如影随形的还有两个字:花冈。
花冈町,如今已改名为大馆市,位于日本东北地区大馆盆地北端,是一个以铜矿山为中心形成的小镇。从1944年8月初到1945年6月,耿谆曾经在这里做过将近一年的劳工。不过让耿谆和花冈真正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是1945年在这里发生的那场劳工暴动。
1945年6月30日深夜,因不堪忍受欺辱虐待,身为大队长的耿谆率领七百多名中国劳工举行暴动,他们打死了四名日本监工和一名汉奸,逃出所住的集中营中山寮。在日本军警的镇压下,暴动最终失败。暴动的前前后后,有四百一十八名中国人被虐待致死,而这一事件的日本肇事者战后也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BC级)判罪,这是唯一一例被国际法庭判为战争犯罪的迫害中国劳工案件,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本土发生的唯一一次中国劳工集体暴动。这一事件被称为“花冈惨案”或者“花冈暴动”。
花冈暴动的领导者,这是历史赋予耿谆的第一个身份。
再次把耿谆的名字和花冈联系到一起的重要事件,发生在花冈暴动五十年之后。1995年6月28日,耿谆与其他十一名花冈暴动幸存者一起,把当年迫害中国劳工的鹿岛组(现日本鹿岛建筑株式会社)告上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这一事件后来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经过长达五年多的诉讼,最后案件以鹿岛组与原告的庭外和解告终。
“花冈索赔案”的首席原告,这是历史赋予耿谆的第二个身份。
因为由日本律师团代表中国劳工与鹿岛组达成的和解中根本没有满足原告提出的“谢罪、建纪念馆和赔偿”三项要求,耿谆拒绝在和解书上签字,并拒绝领取鹿岛组发放的和解金。
为尊严而不妥协的老人,这是历史赋予耿谆的又一个身份。
把这三重身份叠加在一起,耿谆的形象渐渐地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这是一个时常身处大是大非的漩涡中而意志坚定的老人,无论是当年的暴动,还是后来的索赔,抑或是最后的抗争,耿谆始终处在整个历史事件最中心的位置上。
网上搜寻是在我的困惑中结束的,在对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的寻找中,我发现原来已经有那么多人向这个老人投去过了关注的目光:中日两国多家媒体都曾对耿谆进行过专访和报道;在中国和日本,出版的关于耿谆的传记、关于花冈暴动的长篇报告文学也都不止一本;在日本,有根据花冈暴动改编的舞台剧,在中国,有为花冈暴动专门拍摄、由大牌明星出演的电视剧和电影。
2007年3月,我第一次见到了耿谆老人。与之前在网上见过的照片相比,老人的表情中少了些坚毅和凛然,而多了份慈祥和亲切。还有,他比照片上要老些,毕竟已经有两年没有怎么参加公众活动了,而那些照片,最早也是他两年前参加活动时留下的。
尽管已经在大量的文字资料中对耿谆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第一次见面,他身上还是有一种气质强烈地吸引了我。眼前的老人,一举手,一投足,都会让我自然想起“旧式”或者“老派”中国人的样子。这种气质很难从我们的晚辈、同辈,甚至包括父辈的身上嗅到,而在耿谆老人的身上,我一下子就感到了它们的存在。
被吸引之后是我的窃喜,因为我所看到的是网上那些关于耿谆的文字中没有的。这意味着我的写作空间出现了。面对重大历史事件,人们更喜欢陶醉在宏大的叙事中,更喜欢把重点放在对起伏迭宕的事件本身的描写上,而很少关注身处其中的个人。
那一次见面,我们从上午八点一直谈到中午十二点,又从下午三点多谈到了将近七点。前前后后持续了六七个小时。怕老人疲惫,谈话中我曾几次对他说,您觉得累了随时可以停下来。老人说,你们从北京来一次不容易,还坐了一夜的火车。所以我尽量跟你们多说点。然后他又补充道:“你们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我都会尽量回答。”
交谈的内容有时并不愉快,对自己当年的惨痛经历,耿谆叙述时也会激动,会停下来喘息,但是老人没有太多怨恨。相反他总会把自己同当年那些牺牲在战场上或把遗骨埋在异国他乡的同伴比较。
“我很满足。”在交谈的过程中,这样的话,老人说了不止一遍。
尽管从年龄上讲,我们都可以算是老人的孙辈了,但是无论是我们来,还是走,耿谆都会站在二楼的楼口,拄着手杖,身体直直的,目光随着我们。在交谈中,老人坚持用“先生”称呼我和我的同伴,不仅自己这么叫,还让他的儿子孙子也这么称呼我们。
这种老派的品质显然已经成了耿家的家风:那天中午我们在耿家吃饭时,老人的大儿子耿石磊一直在招呼我们吃饭,而他自己却很少动筷子。同时,耿家的女人和孩子都没有出现在饭桌上,任凭我们怎么招呼也不上桌。
“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我能想到的用来形容耿谆老人现在的精神气质最恰当的句子了。这种从容不迫是装不出来的,那来自老人九十三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也来自于他历经生死磨难后的大彻大悟。
差不多和所有来访者一样,我们的话题也是从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暴动开始的。
对于当年暴动前后发生的事情,甚至包括很多细节,耿谆依然能够脉络清晰地讲述给我们。事实上,自从1985年耿谆与日本华侨、当年花冈暴动时他的部下刘智渠重新取得联系后,关于花冈暴动的事情,他就不知道给多少人讲过多少遍了。
不管讲过多少遍,不管对谁讲,老人的认真和投入都是同样的,再说起来,依旧一丝不苟,字斟句酌。
在耿谆老人对花冈暴动的讲述中,他说得即使再少,有三点也是一定不会遗漏的。在他心中,整个花冈暴动中这三件事是最重的,因为它们最能反映中国人的品行和骨气。
其一,薛同道事件。
薛同道是耿谆的工友,在1945年6月上旬的某一天,被日本人活活打死,此事成为花冈暴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在打死薛同道的凶器中,除了木棍、皮带外,一条用公牛生殖器晒干做成的皮鞭引发了耿谆和工友们的怒火。
“日本人用这东西打我劳工,他们这样做有辱我中华民族的尊严太甚。就是在那时候,我下定了暴动的决心,就是掉头,也义无反顾。”在薛同道事件之前,从三月份起,耿谆就一直被要不要暴动的念头折磨着,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难做出的一个决定了。“由于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那时每天都要死去四五个人,前前后后已经死去二百多人了,而躺倒不能动的还有几十名。但是如果一暴动,就把所有人都推到了死亡线上,我实在不忍心。所以虽然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刻,我们还是强忍着。因为暴动其实就是去送死。我是一个千人之长,事情的好坏与我有关,事情做好了算是我做对了,没做好是我有罪,对不起我的国家我的难友,所以我一定要做好。”
当日本监工用手中公牛生殖器晒制成的鞭子抽在中国劳工薛同道的身上时,也终于抽碎了耿谆心中的犹豫。在他心中,士可杀不可辱,民族尊严是一条不能逾越的底线,是必须用生命去捍卫的。
“这叫知耻而后勇。”老人总结道。
其二,为两名同情中国劳工的日本监工更改暴动时间。
在中山寮有一老一小两个日本监工,中国劳工背后管他们分别叫“老头儿太君”和“小孩儿太君”。这两个日本人对中国劳工比较同情。“‘小孩儿太君’年纪当时大约十九岁,曾经管过一段粮食,他心地比较善良,有时会偷出一点给饮事班,给饿病的中国劳工难友吃。而‘老头儿太君’带着劳工挖下水道时,会派人在远处放哨,看有其他日本监工来了,就让中国劳工干一会儿活,没人时就让大家歇着。”耿谆说。
暴动最初定在6月27日,但后来大家发现那天这两名同情中国劳工的日本监工全都当班,耿谆斟酌再三,决定冒着泄露秘密的危险,把暴动时间向后推迟三天。
不枉杀一个好人,这一点连后来审讯耿谆的日本人都非常佩服。
“是咱中国人就该这样。”耿谆看着我说。
其三,在暴动中约法三章。
由于暴动中有日本监工逃脱,他们报警后整个花冈町警报不断,原来耿谆“全体劳工饱餐一顿后再出发”的计划被打乱了。但是就在大家饥饿中仓促整队出发前,耿谆还是给队伍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不人民宅,即便口渴了也要由小队长去要水;二、不准擅自离队;三、不准扰民。
耿谆对劳工们说:“老百姓没有罪,像小孩儿太君我们还去救他,我们不能杀一个好人,我们出去跟拿枪杆子的人拼一场。”在耿谆看来,冤有头债有主,跟无辜的百姓过不去实在不应该是中国人所为。
“咱中国人就不能做这事。”老人说,眼睛依然直视着我。
在讲述花冈暴动的过程中,“咱中国人”是耿谆用得最多的一个词。老人最满意的一点,就是这群长期吃不饱、面黄肌瘦的中国人,不仅在日本人的地盘上上演了一出以死抗争的大戏,而且在暴动过程中没有滥杀无辜、没有骚扰百姓。
说到花冈暴动的失败,耿谆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在人家的地盘上想杀出一条生路几乎是不可能的。
“暴动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就是为了维持中华民族的尊严,没有想着活着。日本四面环海,是跑不出去的。别说七百人,七千人也跑不出去。但是我们就是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可辱。”耿谆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孔圣人的性格,也是积淀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性格。在愤死与苟活的选择中,中国人的一点血性、一点执拗、一点慷慨赴死的气概在耿谆等人的身上迸发了出来。
他们的计划也是自杀式的。“暴动的计划就是跑到海边集结,等着包围。等到日本人围上来,战死。”耿谆说,“没跑到海边,就被日本人抓回来了,算是第二次被俘。”
审讯的时候,耿谆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头上:“暴动是我策划的,指挥的,那些人也是我指使劳工去杀的。要杀你们就杀我好了。”审问耿谆的日本人怀疑他是中国的将官,是中国政府派到日本来搞颠覆活动的。后来他们把耿谆在花冈住的小屋搜了个遍,连地都刨了,也没找到他“勾结”中国政府的证据,但是他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区区七百个中国人就敢在日本暴动。
一个看守耿谆的日本人对他说,你是英雄啊,居然暴动成功了。耿谆回答:“我不成功。要是我们在海边同你们恶战一场,慷慨赴死,那才叫成功。”
当年暴动失败后,耿谆很坦然。在他被抓回警察署,日本警察审讯他之前,他竟然趁着空闲在被绑得结结实实的椅子上打起了盹。日本人来查号,看到这情景觉得很惊奇,对他说,你都马上要掉头了,还居然能睡着。
“因为心里没有事了,我应该做的都做完了。人一放松,就睡着了。”耿谆对我说,说这话时他笑得很放松,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情境中。
第一次到耿谆家里的时候,对于怎么来写这位老人,我还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直觉告诉我,详细记述发生在老人身上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不是我此行的目的。一方面,已经有太多关于花冈暴动的著作问世了,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任务已经被别人完成了;另一方面,对于勾勒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原貌来说,仅仅采访耿谆老人也是远远不够的,那实际上是一个要跨越中日两国,涉及几十、上百人的浩大工程,而以我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来说,去完成这件事,短期内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从采访开始,我就把目光的焦点有意投向了那些有影响事件的背后。在简单地讲述了花冈暴动的经过后,我们开始聊他的家庭、聊他读书写字做买卖的经历、聊他被俘前长达十二年的军旅生涯。对这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在“花冈暴动”、“花冈索赔案”这些耀眼事件之外,还有着太漫长的幽暗岁月,它们默默地流淌在那些重大事件的光影里,静静地等待有人来涉足。
而当我们穿过这幽暗的岁月后,才惊奇地发现,原来那里才真正藏着耿谆的秘密——之所以成为那个三重身份集于一身、在大是大非的旋涡中意志坚定的老英雄耿谆的秘密。
第一天谈话之后,老人执意要送给我们一行人每人一幅字。写字是伴随老人一生的爱好,也是他的待客之道。不管是日本政要还是普通的来访者,一生贫寒的耿谆送给的礼物都是一样的——他自己写的书法作品。
第一个向耿谆求字的是个日本人,名字叫烟义春。那还是在1945年底。
烟义舂原来是日本军队里面的军曹,在中国作战的时候因为有反战情绪,被送回国内,判了刑并关到秋田县监狱。在监狱里面他做杂工,干给其他犯人送饭一类的杂务。他很敬佩同在一个监狱里领导了花冈暴动的耿谆,认为这个中国人是个不怕死的英雄,在生活上有时候就会给耿谆一点照顾,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熟悉起来。
到1945年底,日本战败已经几个月,狱方不再敢把这些中国人当成犯人了。按照耿谆的要求,十二个中国劳工住到了一起,他们的伙食也得到很大的改善。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看书。送书的时候,烟义春会推着放满图书的小车,来到耿谆等人的面前,语言不通,他就拍拍书,意思是问他们要不要。给中国人准备的都是中文书,有中国出的,也有日文翻译成中文的。耿谆在那段时间读了不少书。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耿谆还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本吉田松荫著的《攘夷论》,书中有一首诗和当时他在狱中的心境颇为相似:“自从入狱泉,悉却尘内烦。手中把书读,读倦枕书眠。”吉田松荫是日本幕府末年的维新志士,主张国家要开放通商,因为思想不为当权者所容,被判处死刑,后来死在了监狱里,死时只有三十多岁。“我当时在狱中心情很平静,也‘悉却’了‘尘内烦’。”耿谆回忆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