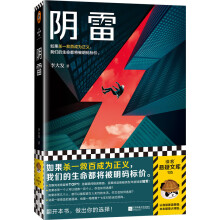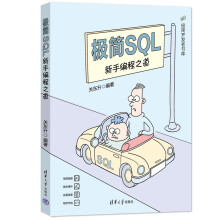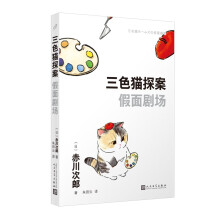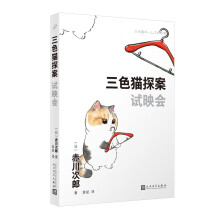第三,是文学史家在撰写文学史论著时所欲寄托的某种思想意义,或评介历史人物和作品时所引发的某些议论,前者与史家的动机有关,后者与史家的心态有关,二者都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说得准确些,是文学史家把某种思想赋予了文学史论著。但尽管这种赋予有恰当与否、合适与否、自然与否之区别,却并非是纯粹主观的,也并非是绝对的外加,因为史家之所言毕竟不可能与文学史的客观事实,与文本、人本毫无干系。任何史著本来就允许(也不可能杜绝)史家主体意识的介入,故在分析文学史本体时也不可完全把这种寄托和议论排除在思本之外-
让我们对此稍作说明。出于某种动机而在文学史中寄托一种思想意义的,可以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为例。黄人生活于清末民初,痛感列强环伺、清廷腐朽所造成的国家民族危亡之局,遂欲以文学救国,而文学史也是他手中的一种武器。他在任东吴大学教授时编《中国文学史》,首先便对“文学史之效用”作了详尽阐述。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九章《中国文学史学》介绍黄人编史的四大目的,是抵制崇洋之风,激发爱国热情,宣扬自由民主和分清精华糟粕①。此时的黄人已认识到,文学与文学所赖以生存的语言文字乃是一种权力,他说“占有国家者,亦必并文学权而占之”②。掌握政治权力者,一定也掌握着文学权,而文学权也就是语言文字权,或日话语权。面对列强的侵略,黄人格外重视传统悠久的中国文学,“国有语言文字.此其国必不劣”,他之争文学权,他之撰著文学史,归根到底是为了“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③。黄人《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处处贯彻着爱国保种之动机.是一部有寄托的学术著作。这根贯穿全书的思想红线,是作者黄人赋予它的,那个时代别的作者虽然未必个个清醒意识到这一点,但其实也往往不同程度地把总结赞扬中国文学与鼓励民气、御侮自强的想法相联系。这种反映着时代要求的思想,对于文学史学的研究者来说,自然不可忽视而应将其列入文学史本体而给以注意。属于这种情况的显例,还有像胡云翼的《唐代的战争文学》。这部被誉为“一部孤愤之书”,“可当作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抗日檄文读”的专题文学史④,出版于1937年。作者写作的动机是有感于“近一两年来中国文坛里充满了非战文学的紧张空气”,他为了反对“那样观世音般大慈大悲的,那样妇人之仁的,那样小孩子般恐怖的,一味慈善主义的非战思想”,“反对卑怯的非战文学,反对那妨害国民性的鼓吹非战思想的文学”而撰写了这部文学史①。此书有选择和有重点地评介唐人有关战争的诗作,或褒或贬,而作者本人则借此提出并发挥了自己的观点,抒泄丁对时势的忧愤和对文坛的不满。史家的思想与文学史融合为一,我们也就不好将他的思想排除在文学史本体之外。属于这种情况的最近例子,是徐培均主编的《中华爱国文学史》,其《导言》云:”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历史使命感敦促我们必须总结历史,正确引导人民高涨的爱国激情,为此,我们特地编写了这部《中华爱国文学史》,试图弥补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②文学史家的爱国思想和古代文学中种种爱国思想的表现合拍、呼应,这自是一部建筑在思本基础上的文学史.
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文学史家在行文中随机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且这意见不一定与文学或文学史有关,却与现实生活有关。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原版下册中屡见的类似段落:“这些作品……完全用客观的眼光去描写灾民种种的惨况,穷人吃树根泥土,卖儿鬻女……而那些从事囤积的富豪大贾,正在利用这个机会买田置产,贩米娶妾- - - -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经济,这种贫富不均的悲惨生活,一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这一段对白,不仅文字好,意义也好,真是借着野兽,骂尽世上一切,痛快淋漓,深刻无比,字字真深,句句实在。负国家的,负父母的,负师友的,不是到现在仍充满着政府、家庭和社会吗?中国的政治、家庭与社会的黑暗与腐化.不就是那种打-半留一半、革命一半妥协一半的人情主义作怪吗?现在任何一个角落里,不都存在着中山狼式的人们吗?”这些引中发挥的议论,既与历史上的文学有关,是从文学史而来,又是出于作者的现实感受,古今在这里发生了共鸣和呼应。这种做法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个人色彩,不但应该允许,而且正是“最具个性才华的”④。这种文字虽然不是每个文学史家所喜所能,在此后统一体制下集体编著的文学史书中更已绝迹,但相信在个人撰史形成风气,作者们的思想日益解放之后,我们的文学史著作会显出更多此类的个人风采。而作者那些由文学史引发的思想,对于文学史学的研究者来说,则不妨作为文学史本体之一的思本予以考察。
……
展开